祂展開翅膀:那些在魚池拓荒的日子 | 維持健康的好方法 - 2024年11月

祂展開翅膀:那些在魚池拓荒的日子
以馬內利啊,祂展開翅膀,遍滿你的地! 以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十多年來在魚池拓荒的日子, 神總是展開翅膀,覆庇受苦的大地, 憐惜、眷顧屬祂的百姓。
十八年,李約和潔子為著福音齊心在魚池開拓,開拓的不只是當地最底層小老百姓生命的荒原,身為服事者心靈世界的荒野,也一併被上帝開展、擴張。原以為忙碌的傳道生活,會掩蓋掉從年輕時原先領受文字事奉的呼召,然而,就在李約認為文才漸失筆頭漸鏽之際,神要她開始動筆,記錄台灣鄉村最底層的小老百姓的故事。精鍊流暢的文學筆法,深厚的文學底蘊,細數在魚池拓荒以來,五、六千個日子的真實經歷。「祂展開翅膀」,是一群鄉下小民生命故事的最佳註解,也是一個鄉村宣教士忠實記錄這些故事最深刻的體會。
走過世紀末的九二一巨震、陪伴鄉下婦女們度過生命的煎熬、處理教會內的紛爭與聚散、面對自己內心的黑暗巨獸和纏繞荊棘,無論哪一種遭遇,哪一個經歷,哪一份心情,李約用筆見證了當患難如洪水滔滔,淹沒一切,人心徬徨無所倚靠時,神展開翅膀,遍滿全地,覆庇受苦的人;神如鷹將祂的百姓背在翅膀上,遮蔽著飽受災難的大地,也護庇著恐懼驚嚇的脆弱人心。神的劇本,雖然總是和人想像的不一樣,不變的是在各樣艱難中,祂從不吝惜施展良善的恩慈,賜下恆久永遠的愛。
經歷過生命的破碎、掙扎,甚至走過苦難和絕望之後的心境,在烽火或者風暴過後滿目瘡痍的凌亂之下,偶然發出一絲綠意,一株小小的苗芽,那個生命的抒發,就是文學的契機。──李約
作者簡介
李約
本名李慧敏。傳道人,嗜書,愛看戲,渴望寫作。打從年輕時便閱讀各類書籍以餵飽雙眼。年輕時參加第一屆青宣,認定自己要以文字事奉神。不料人生道路曲折離奇,曾經潦倒失業靠家人接濟過活,作過學校的助教,當過一陣子戲劇相關工作,出國念過書,回國後還寫過小說。從沒想過會被神呼召進入中華福音神學院,更沒想過會與同學潔子,一同到魚池鄉村宣教。
活在最基層的百姓之中,練就了她用最原始的語言和最簡單的文字,說出一個個樸實無華卻真摯無比的生命故事。文學與藝術一直是她創作的養分,過去的坎坷之路也沒有白走,這些都成為她文字創作最好的材料。將近七年,於《校園》雜誌〈拓荒手記〉專欄發表文章,深受好評。透過伯格曼的電影,她挖掘作為一個傳道者的意義;以張愛玲《傾城之戀》裡的類比,反思九二一大地震後,教會蓬勃興起與假冒為善之間的邊界;藉《燦爛千陽》裡阿富汗女孩的遭遇,看見陪伴並鼓勵被鄉下環境所囿的孩子的重要。每一次的嘗試,她總是將凡夫俗子生命裡未曾發掘的深度與人性,提煉出來。
推薦序──以賽亞書的課堂 蔡麗貞自序──曠野裡的聲音 李約
輯一: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 阿麗 橡樹上的黃絲巾──義仔的故事 滾輪下的含羞草 春雨 大雪過後 交會時的亮光 亮光下的影子 纏繞的蔓藤 湯匙與高跟鞋 一個預備好的人
輯二:你的瀑布發聲,深淵就與深淵響應 就是神蹟 心中的巨鱷 世紀末的傳奇 施行聖禮的女傳道 來自伯格曼的啟發 天天 樟樹旁的對話 有祂在 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告別了,2009年 燦爛閃耀的喜悅──再讀以賽亞書
跋
幕後花絮
關於《祂展開翅膀》的二三事 余欣穎(《祂展開翅膀》責任編輯)
誰是李約?
新手編輯,很榮幸就編輯到一本好看的書,之所以說好看,是因為作者李約很會講故事。李約李姐不僅口齒伶俐,說起故事來行雲流水,流暢度渾然天成,不用口說故事時,她就用筆講故事。有些故事在我們的筆下,可能只是一個平淡無奇的流水帳,但在她的筆下,卻成為一齣齣富含情感堆疊、情節鋪陳、高潮迭起、令人想知道下回如何分曉的戲劇。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印象呢?有些事情,細細回想,便發現早有蛛絲馬跡可循。
還記得第一次見到李姐時,是2006年的校園文字寫作營,李姐那時候擔任小說組的講員。礙於年代久遠加上記性不好,她那時候說什麼,現在似乎忘了差不多了。但印象深刻是,這位傳道人不只會講聖經,還還可以用莫言或一些中國作家的作品,來談時代、苦難與信仰,並且把文學講得這麼平易近人,把人性洞悉得如此透徹,令人感到十分詫異而佩服。
那時,她特別舉張承志的小說《西省暗殺考》為例,清末時發生回民屠殺漢人的慘案,左宗棠被派遣,亦屠殺了不少回民,最終平定回亂。這種記史角度,一直是以漢人的觀點出發的,因而我們從小被教育平定回亂是左宗棠的豐功偉業,卻鮮少從回民的處境來思考這件歷史事件的意義,也忽略了種族間的肅清從來就不是單方面的問題,甚至在歌功頌德間,就沒有去思考不同種族間究竟何謂真正的和平共處。像《西省暗殺考》這種好的小說,就提供了另一種思考觀點和架構,讓我們不致落入單一侷限的思考框架裡頭。信仰,非常需要好的小說來幫助我們轉換觀點,跳脫狹隘的群體觀,學習去成就更大的善。
當時,寫作營結束後,我以為就結束了。從沒想過,能夠有機會再跟這樣一位令我尊敬、充滿文學素養的傳道人相遇。
再見李約
再次和李姐碰面,是今年的一月。去年知道自己要編的第一本書,是李姐的《祂展開翅膀》,又被編輯主管告知,一月李姐會北上,屆時可以跟她吃飯,坐下來好好聊聊她的文章要怎麼成書,心中難免誠惶誠恐。見面前的那個週末,我幾乎就泡在她的文字裡,讀過她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這些文章原本是在校園雜誌專欄發表的文章,從2003年一發表,到2010年才停,一寫就是七年,反覆閱讀著她筆下那些人物生命故事的轉變:潔子、阿麗、義仔、春雨、言歡、心裡……,好像也跟著她參與了在魚池鄉村福音工作七年來的更迭變化。
見面的那天,李姐本著她喜歡分享、善於表達、真摯敞開的性格,一見面就不避諱聊起她的同工潔子生病的狀況,甚至說潔子還比她看得開,認為離世就是回到主那裡,在那裡有最好的獎賞,因而遺囑都寫好了,一切從簡,連要獻上的花也可以免了;反倒是李姐這個要照顧潔子的人,要調整服事重心,也需要轉換心情,氣色看起來比潔子還要糟,經常被人誤認為她才是病人。
見面前惡補猛讀李姐的文章,看到她和潔子十八年前,回應神的呼召,一起從同學到同工,從華神完成裝備到魚池正式開拓教會;當時魚池沒有一間教會,她們兩人彼此配搭的情誼,猶如摩西和亞倫、保羅與巴拿巴的同工關係,令我非常感動。如今潔子生病,她和李姐其實都很不好過,但聽著李姐用輕鬆詼諧的方式說著上帝給他們的劇本,以及她們一步步的調整重心、預備離開親手開拓與建造的教會、退居幕後帶領新同工等等不易的挑戰。或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漸漸發現她們離開魚池,並不是所謂的熄燈或結束營業那樣傷感;她們雖然離開,但在那裡所立下的根基,反而是個起點,讓更多的故事得以繼續發展,讓更多新的可能性得以開展,似乎也不覺得那麼沉重了。
魚池鄉的那個午後 第三次跟李姐碰面,則在三月初。
這次是我從台北下到中台灣的魚池,與李姐洽談《祂展開翅膀》的編輯事宜。會想要親自造訪一趟魚池鄉,是因為想要在這本書裡增添一些照片,讓讀者在讀李姐濃厚綿密的文字時,能有些停頓呼吸的空間。平時或多或少有在拍照,想當然也可以從舊有的圖庫中,找一些風景照或是花草照使用,但搜尋時怎麼樣就是覺得不對勁,少了一些魚池當地的味道。因而,很倉促地於前一個禮拜問李姐能否到魚池一趟。熱心的李姐雖然要照顧不停進出醫院的潔子,卻仍迅速幫我們聯絡好魚池禮拜堂的同工,讓我們當天可以借宿一晚,順利成行。
那天,聊了許多。李姐談到她從小就是嗜「字」如命的小孩,照她媽媽的說法,只要有字的東西,她幾乎就會拿來讀。直到有一天,她讀到王安憶曾經用「餵飽自己的雙眼」,來形容這樣的狀態,覺得非常貼切。大學時,她是標準的文藝青年,留著一頭長髮,喜歡穿著長裙。她笑說:「大概就是有點像齊豫那類的氣質吧!」常常泡在咖啡館裡閱讀和寫作,一寫就是八千字。
後來,喜歡俄國文學的隨行企劃同工,和李姐聊了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也談了《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裡面的信仰意涵。我則跟李姐聊起了柏格曼。
電影中的心靈交會
第二次跟李姐碰面時跟李姐提過,她所有的文章中,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來自伯格曼的啟發〉,因為我也喜歡柏格曼。記得當時李姐回我:「她寫過所有的文章,也最滿意柏格曼那篇。」但接下去就帶著不解的納悶與疑惑問我:「但是為什麼?柏格曼很老欸……。」言下之意就是,年輕如我應該不會喜歡那些過氣的老人家,或者也意味著可我太年輕,能夠體會柏格曼在電影裡頭要表達的東西嗎? 這次見面,我有機會跟她說明,為什麼我會喜歡柏格曼。雖然只是一次無意間看到《野草莓》這部電影,發現這位導演的敘事步調,很符合自己看電影能夠思考的速度,也覺得很難得有一位導演,如此認真地去思考關於生命和信仰的問題。
《野草莓》和《第七封印》同一年完成,那個時期柏格曼對信仰的思考雖未明確,還是丟出了某些石頭,泛起了些許可能性的漣漪。他的電影往往反映出他真實人生的紊亂與難解,即便柏格曼自身最終走向虛無,但透過電影,他似乎也比其他人都更認真嚴肅地去看待自己所遭遇的問題。或許若沒有電影,柏格曼的生命會是更加找不到出口。透過電影藝術,柏格曼才會是柏格曼。
不知道為什麼,結束那天的聊天後,李姐突然跟我說:「欣穎,不瞞妳說。一月我們第一次見面,看到妳時,我心中在想,這麼年輕的一位姊妹來編我的書,她會懂得我要表達的嗎?不過經過上次和這次跟妳聊天後,我很感謝主,妳懂的。」
風暴過後的那一株苗芽 年輕時作為一個愛好寫作的人,李姐說她一直記得張愛玲說過的:「出名要趁早。」
歷經魚池十八年的事奉歲月,李姐的寫作風格和動機,都變得和年輕時的寫作非常不一樣。不是為了成名,而是因為上帝要她寫下這些故事。我雖然無從讀到李姐年輕時的文字,但想起了書名會時,曾摘錄李姐的一段文字,表達這種轉變:
走過為賦新辭強說愁的寫作階段,經歷事奉底層小人物後,如今更加明白文學與寫作的意義:「原來苦悶的象徵並不是指那種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辭強說愁,乃是經歷過生命的破碎、掙扎、甚至走過苦難和絕望之後的心境,在烽火或者風暴過後滿目瘡痍的凌亂之下,偶然發出一絲綠意,一株小小的苗芽,那個生命的抒發,就是文學的契機。」
李姐如今半百年歲,終於要出第一本書了。而我卻想說,我真的很榮幸,可以成為李姐第一本書的編輯,也可以第一次當編輯,就編到如此精采的一本書。
滾輪下的含羞草天還沒亮,我聽見窗戶那裡有人在敲,很輕的聲音,敲了兩下,停頓一會,再敲幾下。我過去打開窗,是秀青。趕緊開大門讓她進來,見她臉上一大片瘀青,眼睛底下黑了一塊。「他又打妳了?」潔子從玻璃櫥櫃找出藥箱,我去溫一杯牛奶遞給她。秀青尚未開口就哭起來:「每次都是這樣,他前天到我娘家窗口叫我出去,我不肯,他就跪在那裡跪一整夜。可是我一回家,情況還是跟以前一樣。」潔子整理著瓶瓶罐罐,把紗布裹好收起來,問她:「那這一次妳準備要怎麼辦?」秀青低下頭來:「我還是想要離開他,我受不了這樣折磨……。你們上次講的那個婦女中途之家,我去好了。」秀青的丈夫文祥有吸食毒品的問題,我們自從認識他們這一家之後,持續關心他們、幫助他們。然而,我們也越來越感覺無力再幫下去:他們的模式反覆如此,文祥沒錢買毒品的時候,總是跟秀青伸手要錢,不肯給錢就遭他拳打腳踢,秀青就跑回娘家。娘家也不遠,就在一條街外的距離,娘家的人總是義憤填膺一番,發毒誓非要了斷他們兩人的糾纏。其實他們的三個孩子早就在外祖家裡,這對夫妻無力照管他們。文祥總趁著夜深人靜之際,跑到岳家三合院的埕子邊,他一吹口哨秀青就會出來,抱著他哭,乍看好像都是旁人拆散他們似的。文祥這時總是訴說心聲,苦苦哀求妻子回來,而秀青也總是熬不過他的懇求,一次又一次心軟相信他這一回必定洗心革面,就跟著回去;然後故事再重演一遍,又一遍。認識我們以後,他們似乎找到一條出路,有一陣子夫妻兩人都跟著我們讀聖經、參加聚會。特別是秀青,我帶領她一對一慕道課程,她對上帝的話語很有反應,願意信主也勸文祥信主,他們都準備要接受洗禮。這種現象,當然也大大激勵我們這兩個開拓教會的女宣教士,更加賣力探訪關懷他們。文祥並不是那麼穩定,他努力過,試圖振作起來,也想好好工作賺錢養家,可是沒有幾天遇到什麼不如意,就又回到毒品裡頭。那些做慣他生意的人也不會放過他,不時就要找他去泡茶聊天,然後在桌子底下完成交易。這一年暑假,就讀神學院的正修、雪妮夫婦來到魚池實習,正修過去曾經吸毒坐牢,在監獄裡悔改信主之後,立志奉獻作傳道。他跟文祥一見如故,非常談得來。正修建議我們要讓文祥進晨曦會戒毒,我們跟秀青一起鼓勵他去,文祥也已經點頭答應了,就在要去的前一天失蹤,之後關起了門,拒絕我們所有人的探訪和關懷,也禁止秀青再跟我們有任何聯絡。秀青告訴我們,這一次是她偷跑出來的,他把窗戶釘上木板條,大門封死;秀青半夜起來搖下了一塊鬆動的木板,從窗戶爬出來,找到福音中心這裡。我們答應天一亮就去聯絡曾經介紹過的社福機構,但聯絡過後還沒有找到秀青,就聽說她又回去了。然後,故事又重演一遍。秀青的妹妹秀紅也開始來找我們,談她姊姊的問題:「不是只有那個鍾文祥有問題,我覺得我姊也一樣有問題,她根本離不開她丈夫,我媽說他們兩人是相欠債。」 她停頓了一下,想一想還是說了:「我覺得鍾文祥一定用了什麼邪術,不然我姊怎麼都走不出來?真是邪門。」
 糖尿病對症飲食:從主食到點心,美味...
糖尿病對症飲食:從主食到點心,美味... 改善膽固醇‧三酸甘油酯對症飲食:從...
改善膽固醇‧三酸甘油酯對症飲食:從... 濟陽式7天有感!不發胖、不生病的飲...
濟陽式7天有感!不發胖、不生病的飲... 料理王國
料理王國 高血脂之健康御守
高血脂之健康御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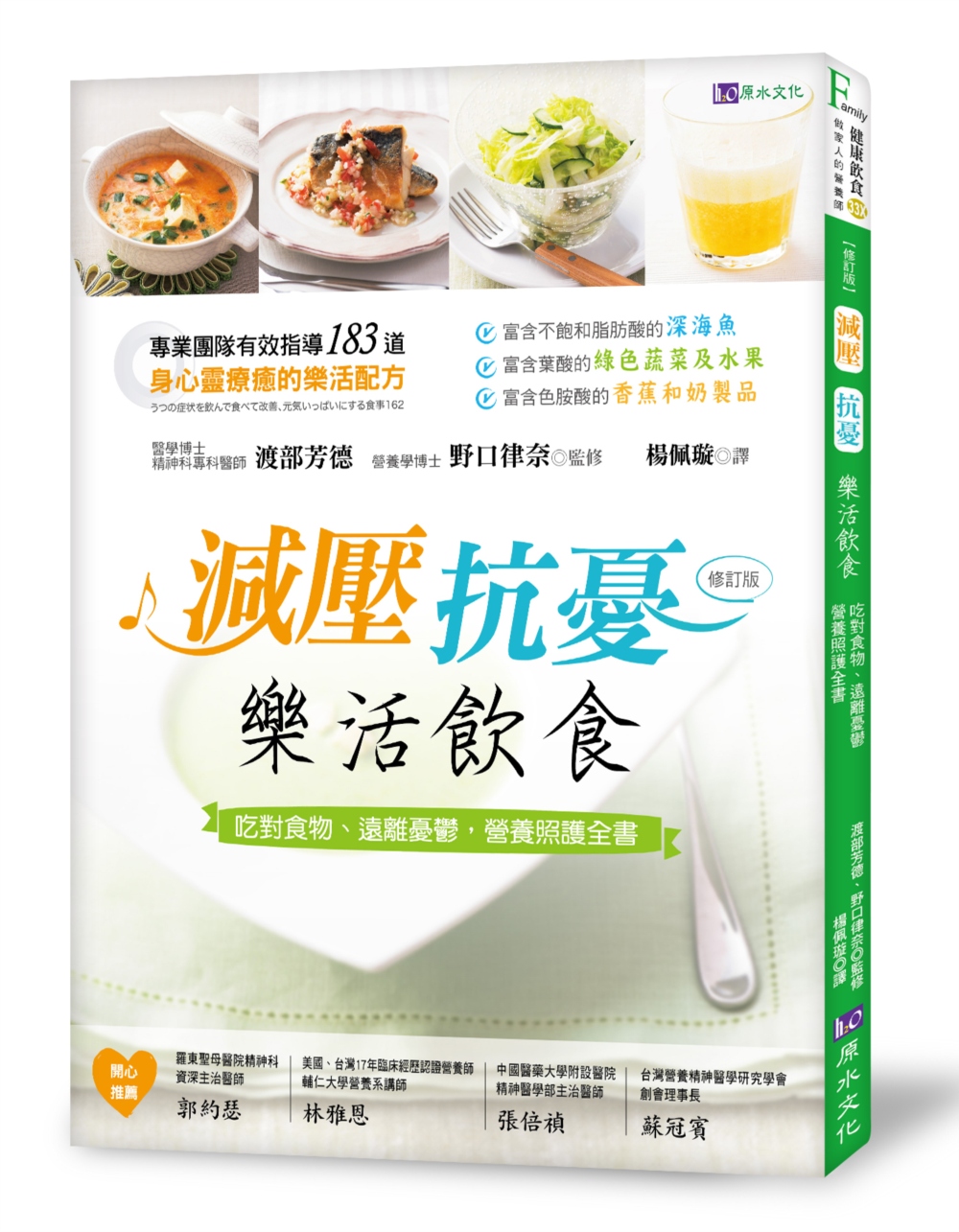 減壓、抗憂 樂活飲食:吃對食物、遠...
減壓、抗憂 樂活飲食:吃對食物、遠... 青花魚教練教你打造王字腹肌:型男必...
青花魚教練教你打造王字腹肌:型男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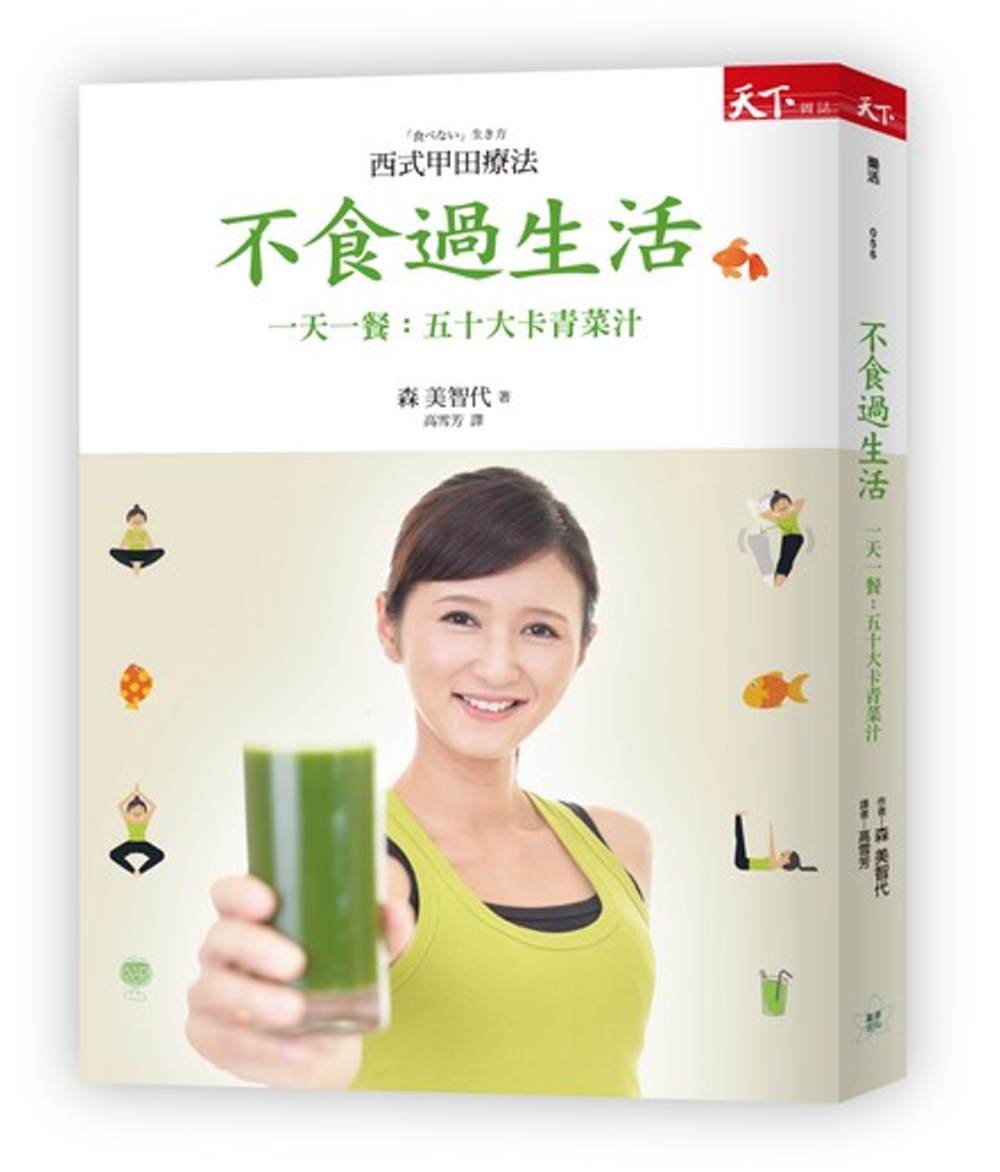 不食過生活:一天一餐,五十大卡青菜...
不食過生活:一天一餐,五十大卡青菜... 免疫營養生酮飲食:理論基礎╳實驗依...
免疫營養生酮飲食:理論基礎╳實驗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