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 | 維持健康的好方法 - 2024年11月

邊緣
在《邊緣》一書中的主要人物──曼歌、飛邊的父母、飛邊本人──都富有想像力,都有令人佩服的獨立性,也都古怪難測。謀殺事件對他們每一個都是一種轉變。他們在自覺過程中追究神秘──一方面是性、酗酒、死亡及絕望,另一方面是則是愛(與性)、自然、藝術和美──其間的言行出乎他自己,也出乎讀者的意料之外。──摘自華盛頓郵報 諾門先生行文乾淨、透澈、他把飛邊的鬧劇寫得有血有肉。故事中的怪誕細節──從各個角色的別致名稱到這些人物的怪癖──雖使本書蒙上一層童話的色彩,而書中的許多人物雖然都只是過場性質,但諾門先生生卻能運用他那準確的敘述本能把這些成分織成一個兼具寓言味道及新聞特寫之即時性的故事。這部迷人的小說好比讀者心中亮閃閃的一盞夜燈。──摘自紐約時報 飛邊永遠都是鳥畫家──「神為了幫助我釐清我的世界,所以賦予我一點點才華。」他曾在某個關鍵時刻如此說──但最後,他卻用這一點點才華做了另一件大事:一面呈現一切經過的璧畫。那是一面滿是小人物的璧畫,其中每一個人都是自然之本貌。這下是諾門的功力所在,他對一幅畫的敘述令我們為之所動,我們既感受到戲劇的高潮,也體會到妥協的氣息。──摘自洛杉磯時報 在諾車先生所舄的《邊緣》一書中,有細節的連吉都有其不得不然的必要。諾門按下一道強韌的前提──良善的人會因激情所驅而失足──其張力處處可見。「良善的人會因激情所驅而失足」,這其實是我們這個使用安全氣囊但高速衝撞的脆弱文化裡的一句格言。《邊緣》透過藝術設法得救贖,它真的做到了。──摘自紐約時報部分內容提要:謀殺 潑左嘔出血,他的頭前拉後扯的,接著他東倒西歪的往前移動,像要鬆掉他那身塵世的形骸似的,然後,他又猛吸一口氣,好像設法再把形骸吸回來。子彈卡在他的肩附近,但並沒有傷及他的喉嚨,所以他還能發出聲音,「我會把我的靈魂付給魔鬼兩次,為的是看到你被吊死。」那句話似乎花了永恆的時間才說完。 那是九月中一個沁涼的早晨,我一夜未眠。事實上,吃完晚餐之後,我就一直不停的喝咖啡,我大概不曾這麼狂飲過。天一亮:我就往曼歌的家走去。我知道乙諾已到北方去了。我重重的敲她的門,直敲到門上的粗木把我的指節刮擦得流血。 「我聽到了!」她說。「等等!女孩子應門時總該穿好衣服呀!」門開了。曼歌穿著睡衣。「肯定是你,飛邊。」 「拜託你現在就跟我划船到薄荷灣。我需要你幫我理清思緒。」 「為什麼一定要到那裏呢?」 「那裏避開龍蝦船,附近沒有人。」 「就是我們兩個小學生,分享一些不乾不淨的祕密,是不是?」 「是的,就我們倆。」 她讓門開著。我看到她套上雨衣和雨靴,然後從書桌的抽屜裏拿出一把左輪手槍。 一出到外頭,她就把左輪槍從一個口袋換到另一個口袋,她的動作很慢,因此我全看在眼裏。她看著我,聳聳肩。「海番鴉今年逗留得晚,你一定已經注意到了,」她說。「而我的晚飯也還沒著落。」 風勢已加強,但我們還聽得到空氣中的鷗叫。在我們下碼頭去的路上,我們勾臂繫擁著,但因為有霧而稍微絆腳。接近碼頭時,我們聽到小漁船撞著樁基的聲音。 「我們就用那隻船吧,」曼歌指著一隻小漁船說。這隻船好好的緊靠在堤防上的繩樁。在一張坑滿了水的艙蓋布底下有一隻備用槳。漏水在艙底形成一汪水。船欄上有鷗糞的白漬,被鷗踩過的糞都碎透了。我們爬進去之後就面對面。 「我想我快生病了,」她說。她的睡衣揚起。她的雨衣大開。她的臉發紅,出汗。幾卷頭髮貼在她的額上。「你看起來也不頂好。」 「我昨晚喝了三十杯咖啡。」 曼歌划船。薄荷灣在往北大約半哩處。灣名本身就充滿希望;甚至在那麼清涼明朗,風往海上吹,整個灣瀰漫爛海草味道的一天,依然如此。半途中,曼歌讓船漂著。「飛邊,你邀我赴這麼一個甜蜜的愛情約會。而且又是這麼一大早。我猜你簡直是等不及要見我了,是不是?」她用一根指頭溜過欄杆,揚起一片白粉。「每隻耳朵後面部要來一點,」她邊說邊把白粉當香水似的抹上。 「把它洗掉。」 「我絕不這樣做。」 陸地的輪廓逐漸成形,嶙峋的雲衫,懸崖峭壁;善知鳥、海鳩、刀嘴海雀,四處都是,活像襯著黑色岩面的五彩碎紙。可以看見數隻龍蝦船,曼歌划著甩掉那些船,然後收起船槳。接著她把左輪手槍放在她的大腿上。 「那裏,」她低聲說。 她指向一群棲在浪潮上的普通海番鴉。她從口袋裏掏出一條包滿子彈的手帕,上子彈,旋轉彈筒,然後把手槍放回她的腿上。她對我目不轉睛,一隻大姆指摩搓著另一隻大姆指。 「你畫過海番鴉,」她說,「我們現在就到這裏來殺幾隻。不過你那位英雄,奧德邦,他也做過同樣的事。」 「沒錯,他的鳥畫並不全是寫生。」 她突然把左輪指向我的臉,然後晃了晃,瞄準遠方的燈塔並說,「砰!砰!」把左輪放下之後,她轉身看到我為之震驚。 「飛邊,看在老天爺的面子上。你父親這會兒正遠赴安替科斯,希望多賺點錢張羅你那該死的蠢婚約,讓你娶那位他們擅自安插的第四代表妹。而同時,你自己的母親卻跟潑左‧敖格思上床。在上面那裏放送留聲機唱片。親親熱熱的,他們倆。而且自從鷗可泥出門之後,她就從未出現在你的早餐桌上。」 「那些都是我老早就吞下肚的事實。」 「而且這些事撕碎了你的五臟六腑。什麼時候想要,你都可以來借這把槍。」 她把手臂伸得直直的,隨即開槍射下一隻海番鴉。她把船划向這隻鴨,其他的則紛紛飛走,然後突然又棲息在大約十碼之遠的地方。她用一隻槳的槳葉把那隻死鴉舉高,然後丟到一只木桶裏。 「我們把這第一隻死鳥取名叫潑左‧敖格思,怎麼樣?」 「我們不取什麼名字吧。曼歌,今天雖然早了一天,但今天晚上我也許可以跟你在一起。」 「恐怕不行。我還是比較喜歡像平常那樣,維持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這樣才可保持熟悉的生活。」她遞出左輪。「想不想來一槍。」 「不用,我看就好了。」 「正如我想的。」 那些鴨子好像是在嘉年華會的壕溝裏浮動的機械鴨似的,她又輕易的快速收拾五隻海番鴨。她再上子彈。桶子裏此時已塞得滿滿的。她把這些鳥都倒入一只大麻袋裏。她把雨衣釦到最上面而且在發抖。 「我一定快生病了,」她說。「也許我們該划回去。」 「不!如果是發燒,我就要儘快把它弄得更糟。我的想法是,愈早搞到那種地步,就愈快好。待會兒我也許會吞下一些吉列特商店那種讓我的尿色不對的藥物。不管有沒有發燒,我明天晚上都等你來。我要繼續與這個村氣的傻子睡覺。主要是憐憫之故。」 她打呵欠。她用睡衣的下襬擦了左輪之後,就拿著它在我面前揮動。「至於這個,如果你能有所決定的話,就讓我知道那個決定。」 她揉搓著手臂。「我覺得我體內開始痛了起來,」她說。「我想待在家裏。升一把火並把這些霧濕的衣服弄乾。也許還要清理這些鴨子。接著就是洗個熱水澡,睡一會覺。而且我不要?不要?你跟我一起走。」 在她划得更賣力時,我說,「曼歌,我愛你。」 她放聲狂笑。「你愛我,但那怎麼辦呢?你就要在哈利法克斯的一家旅館結婚了。你當面告訴我這事的,記不記得?好啦,到時候一定要寫一張明信片給我,由我父親遞送,確實告訴我你和新娘子度蜜月的房間號碼。這樣,將來我也可以和某個蠢蛋在同一個房間睡覺。在我把你,飛邊,忘記之後很久,很久的將來,不過我是不會忘記房間號碼的。你也知道的,我是個記帳的,對數字很有一套。再說,我老早就想去哈利法克斯看看。」 曼歌在更衣。她喜歡在我面前穿衣。那是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的傍晚。我們要去參加一年一次,在拉扣特的穀倉舉行的舞會。她套上一件領口、袖口及下襬鑲有花邊的紅色洋裝,一面還看著我說,「舌頭被貓叼走了嗎?」 「沒有。我只是在想海倫‧湍波瀝曾跟我說過的事。」 「說什麼呢?」 「說你喜歡她的各種迷信:而且甚至還特別留意其中一、兩種。」 「那些大可以說是迷信。但海倫幾乎是靠那些過完她的一生。」 「這我知道。她說如果你要讓一個人不幸,你可以從你的鞋子抓下塵土,然後把它拋過肩並且直對著那個人的方向。海倫說你很仔細聽這個說法。接著你就彎下身,從你的鞋子摳出塵土並扔出去,但卻有一粒東西對著你飄回來。結果你的眼睛進了東西。你非常震騖。」
白眉鴨寇拉‧哈粒摩爾斯電碼潑左與埃樂荔海倫‧湍波謀殺咖啡我的婚姻調查庭蓋佛克節的悲劇無厘灣的鳥宜撒‧司卜拉格突然,極強烈的,他頓時渴望,不論天雨不雨,不計任何代價。都要置身於幽谷之中:獨兒的。~《鷺》~喬其歐‧巴薩尼(Giorgio Bassani,一九一六~,義大利小說家~譯註)
(北國的激情)~以紐芬蘭為背景的《邊緣》好比義大利歌劇 曼歌‧罕多是近年罕見、令人印象深刻的小說人物。她是十足的不讓鬚眉,在鎮上開槍胡射。她的情人帶來一幀他父母相中的準媳婦相片,她用左輪把姬射得粉碎。此後又射了兩槍,射出浩爾‧諾門這部野心勃勃的驚人小說。 曼歌大半時候都醉醺醺,但威士忌似乎沒有使她的心遲鈍,她仍然可以道出家庭內的真相,床上功夫也依然了得。酒精只是減緩她扣扳機的手指而已。她活在本世紀之初,不是在蠻荒的西部,而是在偏遠的紐芬蘭,在一個叫無厘灣的小村子裏(只有一家商店、一家餐廳、一處鋸木廠及一處乾船塢︺。她的情人是敘述者飛邊‧媧司,他大可以成為荒謬文藝小說的主角。飛邊從八歲起就把大部分時間都消磨在狹灣或沼澤地做鳥的素描,然後畫成工筆畫,賣給雜誌社。在外表平靜的生活裏,他遇上了曼歌,同時他本身又是搖擺不定的性格,最後終致失足。 此外,飛邊還有一位性感、直言不諱的母親,埃樂荔。就在飛邊的父親外出為兒子那樁不情願的婚禮賺取費用時,埃樂荔就與燈塔的看守潑左‧敖格思住在一起。潑左是浪漫種子,可以把船隻引離險灘,會以他那沈默的魅力及留聲機唱片誘惑女人,從而改變那個荒遠村落的平靜狀態。「一位燈塔看守總給人一種神聖的信任感,」諾門寫道。「狂飆的強風,茫茫的大霧,仙裏仙氣的風暴,甚至蜿蜓盤旋的水龍捲?數個世紀以來溺沒水手、愛人、漁夫,而且事實上無時不日日夜夜重擊無厘灣的天候狀況?就是潑左必須與之爭鬥的東西。」曼歌也上了潑左的床,而且在關鍵時刻把那支槍拿給受折磨且矛盾的飛邊。 《邊緣》曾被選為電影劇本,但其實應該編成歌劇。這本小說具有十九世紀的大歌劇所具有但現代音樂劇卻付諸闕如的每一項特點:紮實的情節、嫉妒與復仇的強烈傾向、一汪待機吞噬的大海,以及兩男兩女的生動角色。 事實上,這本書不僅是一則老式的故事,也是對北國的詳細頌讚。諾門的第一部小說,《北方之光》,也是寫加拿大:他深愛荒遠之地。《邊緣》裏的地名?薄荷灣、鞋灣、里奇布克托、垂斯巴希?卻如鳥名與人名,予人特殊的愉悅。多種奇異的鳥使故事自成一格:小野鴨、秋沙鴨、三指鷗、鸕★。鎮上的男人在迷霧中搜尋一艘走失的小船時,彼此唱名尋蹤:「力奇蒙‧佛非特,我是阿力佛‧帕湄利。」「阿力佛‧帕湄利,我是飛邊‧媧司。」 這種海上之唱在故事的高潮處一再出現,刻劃出諾門極獨特的小說手法。他的小說雖是誇張的鬧劇,但他的筆法嚴謹,簡潔,且深具寓意。鳥、海灣、專有名詞,雖是怪異的魅力,但卻活生生。摘自「Time」書評
 耳鼻喉醫學講座
耳鼻喉醫學講座 12個孩子的老爹商學院
12個孩子的老爹商學院 正確呼吸,調節自律神經:日本中西名...
正確呼吸,調節自律神經:日本中西名... 吃菜比吃藥好
吃菜比吃藥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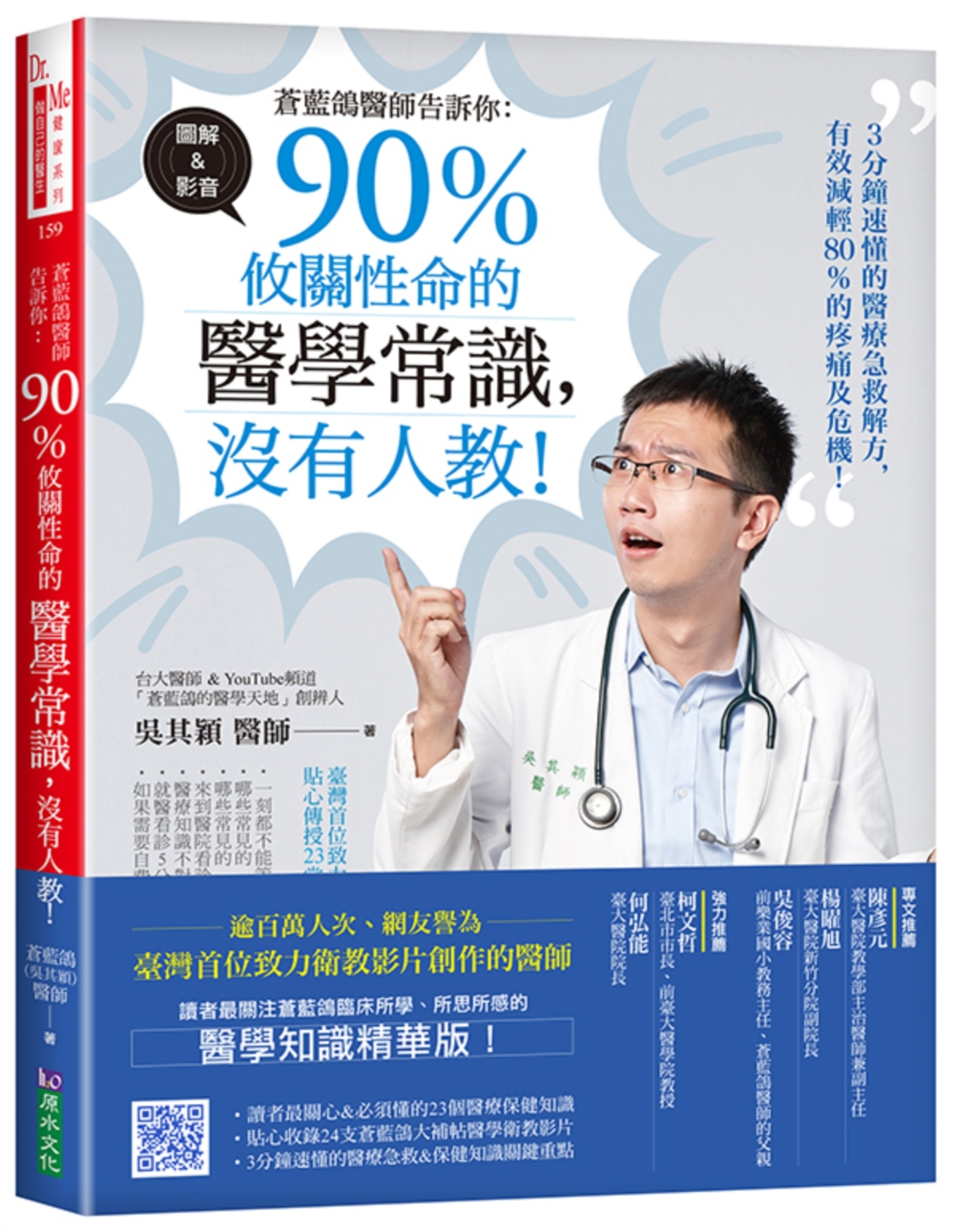 蒼藍鴿醫師告訴你:90%攸關性命的...
蒼藍鴿醫師告訴你:90%攸關性命的... 寶寶這樣吃最健康:歐陽英老師的全方...
寶寶這樣吃最健康:歐陽英老師的全方...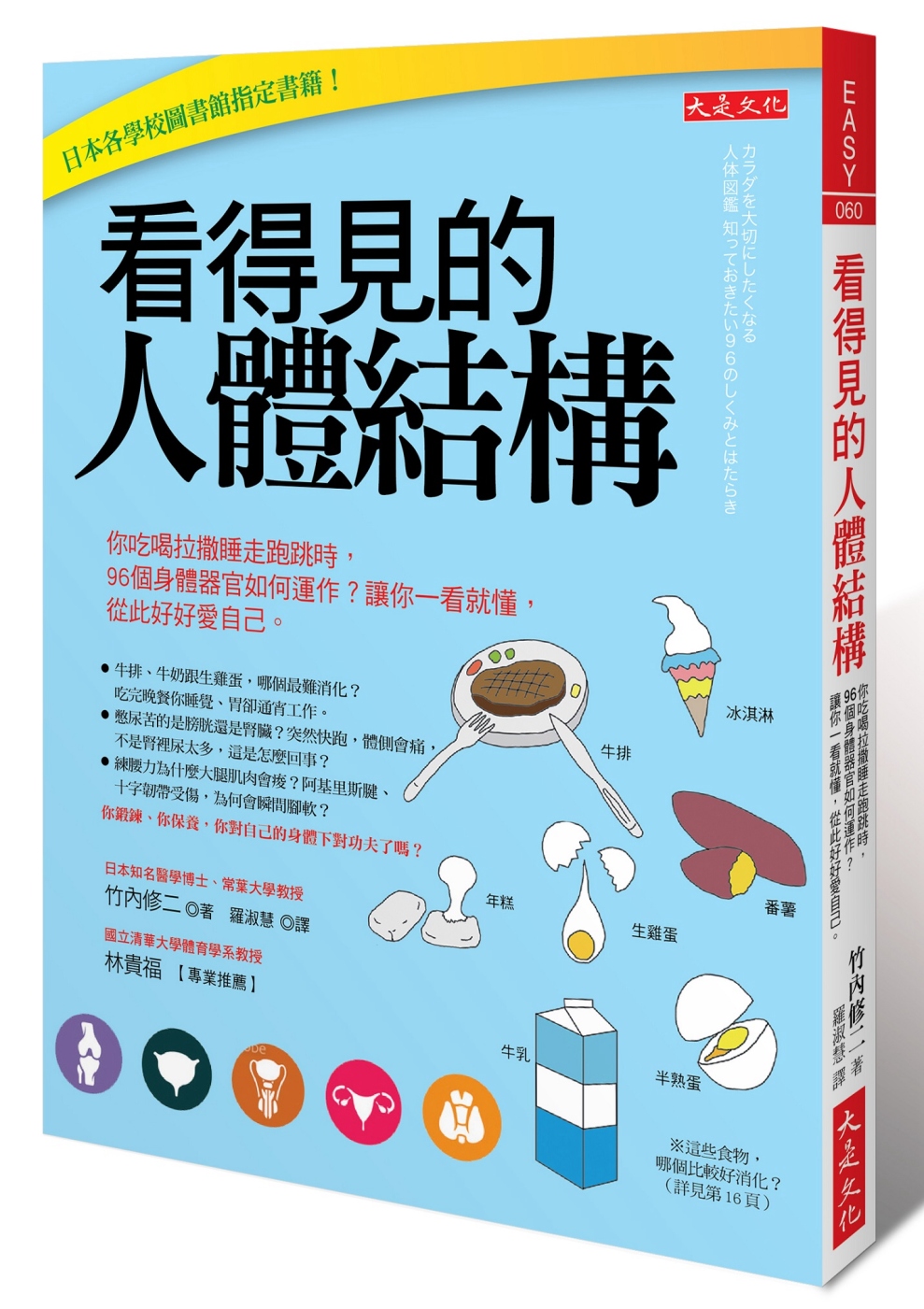 看得見的人體結構:你吃喝拉撒睡走跑...
看得見的人體結構:你吃喝拉撒睡走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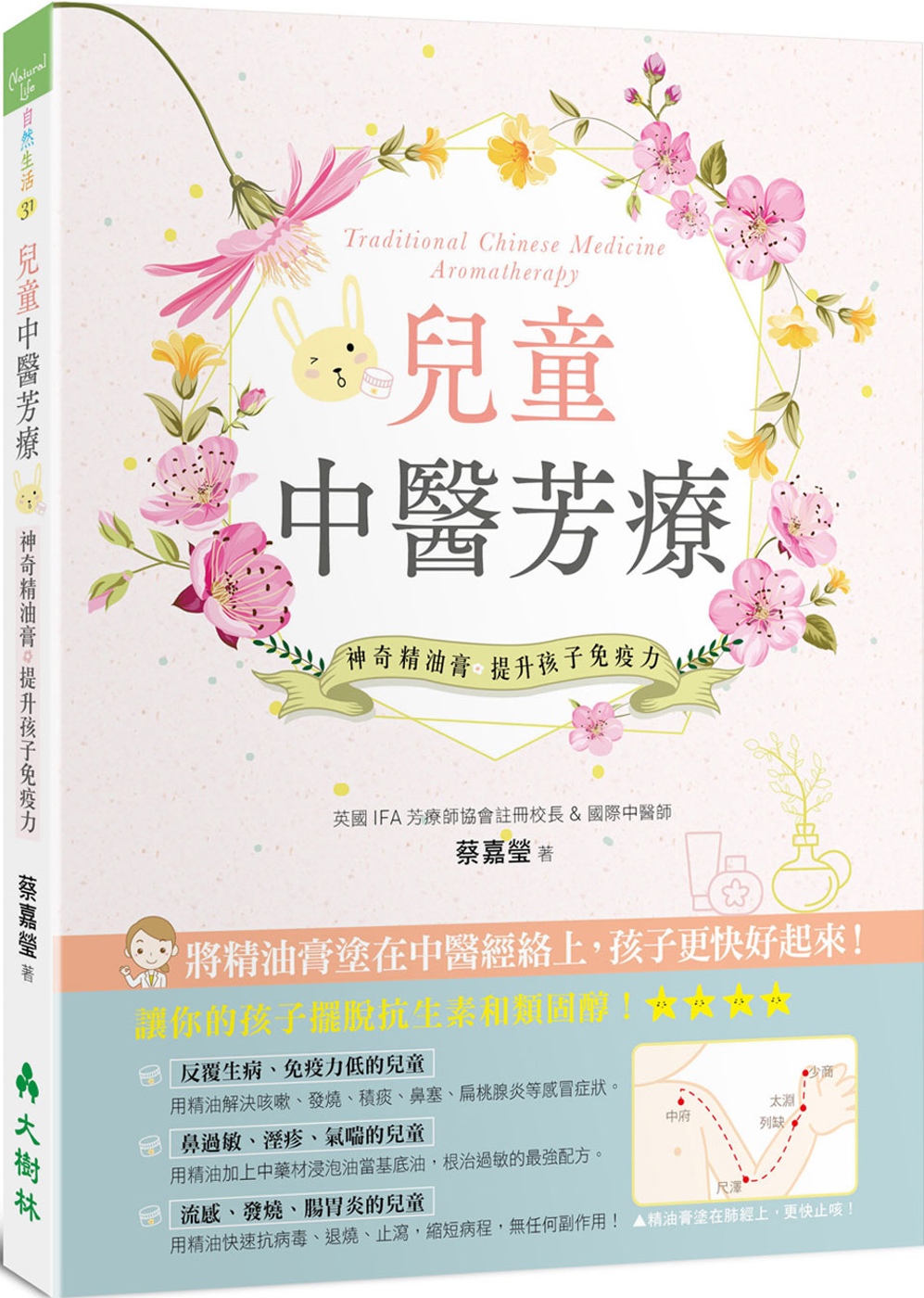 兒童中醫芳療:神奇精油膏提升孩子免疫力
兒童中醫芳療:神奇精油膏提升孩子免疫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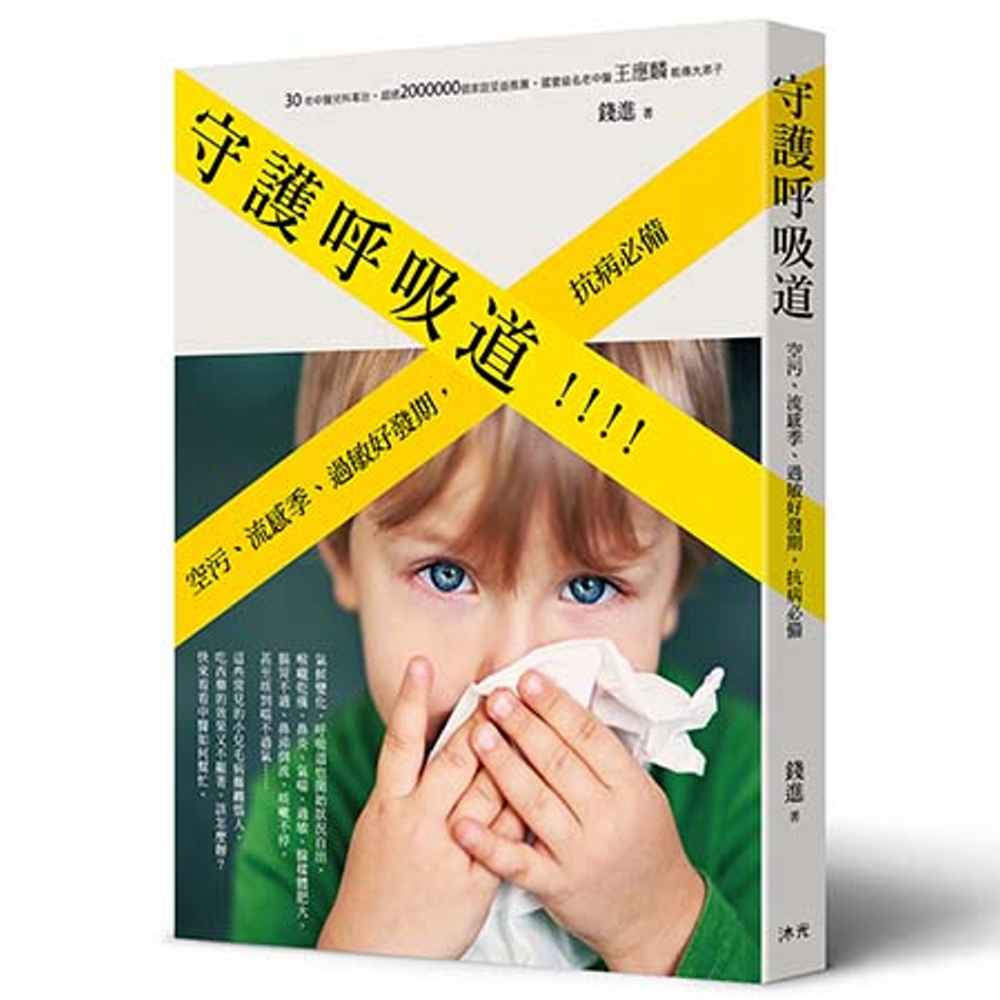 守護呼吸道
守護呼吸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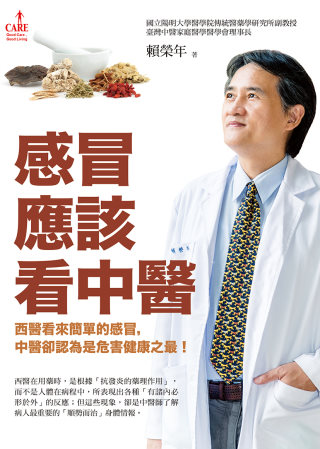 感冒應該看中醫:西醫看來簡單的感冒...
感冒應該看中醫:西醫看來簡單的感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