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香 | 維持健康的好方法 - 2024年7月

天香
細緻似刻字於米粒上,恢弘如一部生命史詩! 媲美《紅樓夢》的雅情氣度, 書寫上海第一人──王安憶, 《長恨歌》之後,又一上海傳奇經典!
「我要研究的是,一戶這樣的大戶人家,究竟是怎麼落敗的?我寫了他們對奢華的無限追求,表現在很多細節描摹上,但我無意把他們放在道德中去進行衡量,說到底聲色犬馬的一切,我是喜歡的,它是道德之外的一個世界。」--王安憶
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至康熙六年(一六六七)的上海興起造園風氣,申姓仕紳家族也隨俗打造一座「天香園」,園中種桃、製墨、養竹、疊石,……
天香園的主人申明世之長子柯海,與南宋康王一脈的徐家之女小綢結髮,卻因柯海納江南的閔女為妾,夫妻之間感情從此決裂,形同陌路;而小綢因與申家次子鎮海的媳婦情同姊妹,在性格厚道的鎮海媳婦穿針引線下,弭合小綢與閔女之間的嫌隙,三人遂以閔女巧奪天工的繡藝奠定「天香園繡」名號之基;而柯海兄弟鎮海因具與世無爭的淳厚性格,於妻子閔氏辭世後,遁入空門;而鎮海之子阿潛託付予小綢撫養成人,後娶了杭州的希昭為妻,卻在一個傾聽「弋陽腔」戲曲的月夜之後,無聲無息地跟著唱曲人隱沒在人世裡……
這是一個男性缺席而由女性頂天持家的故事,究竟三代的女人具備何種功夫,得以讓香火延續?
天香園中的「好男好女」各自經歷怎樣的曲折,方頓悟出生命自在花開花落的平凡幸福?
《天香》的結局沒有大痛苦、大悲憫;有的是大家閨秀洗盡鉛華後的安穩與平凡。傳奇不奇,過日子才是硬道理。《天香》文字婉約如詞、情節幽深如鏡,如此動人心魄的巨作,是部反璞歸真與渾然天成的小說。不慍不火的敘事且不鑿痕跡地耙梳生命之奧義,一路細細品讀,玉潤珠圓的字裡行間,啟示我們體悟得生活與人世,看似平淡實則深刻的生存況味。生命之所以精彩與重要,是因為懂得欣賞那些被忽略的細枝末節微小事物。
我們不得不撫掌承認,大器、華實、優美的《天香》,說穿了我們最熟悉也最陌生的世故人情!
作者簡介
王安憶
一九五四年生於南京,五五年隨母親遷至上海,文革時期曾至安徽插隊落戶。曾任演奏員、編輯,現專事寫作。作品曾多次獲得全國優秀小說獎,是八O年代以來,大陸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
【重要作品】 《紀實與虛構》、《長恨歌》、《憂傷的年代》、《處女蛋》、《隱居的時代》、《獨語》、《妹頭》、《富萍》、《香港情與愛》、《剃度》、《我讀我看》、《現代生活》、《逐鹿中街》、《兒女英雄傳》、《叔叔的故事》、《遍地梟雄》、《上種紅菱下種藕》、《小說家的讀書密碼》、《啟蒙時代》、《月色撩人》等作品。
【作品得獎紀錄】 ◆《長恨歌》曾榮獲九O代最有影響力的中國作品、一九九八第四屆上海文學藝術獎、一九九九年亞洲週刊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00強、二000年第五屆茅盾文學獎、二00一年第六屆星洲日報「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
◆《富萍》榮獲二00三年第六屆「上海長中篇小說優秀作品大獎」長篇小說二等獎。
虛構與紀實——王安憶的《天香》文◎王德威
從一九八一年出版《雨,沙沙沙》到現在,王安憶的創作已經超過三十年。這三十年來中國文壇變化巨大,與她同時崛起的同輩作家有的轉行歇業,有的一再重複,真正堅持寫作的寥寥無幾。像王安憶這樣孜孜矻矻不時推出新作,而且品質保證,簡直就是「勞動模範」。骨子裡王安憶也可能的確視寫作為一項勞動——既是古典主義式勞其心志、精益求精的功夫,也是社會主義式兢兢業業、實事求是的習慣。
早期的王安憶以書寫知青題材起家,之後她的眼界愈放愈寬,四十年代的上海風華、五六十年代的新社會蛻變、文革運動、上山下鄉,改革開放、乃至於後社會主義的種種聲色,無一不是下筆的對象。她的敘事綿密豐瞻,眼光獨到,有意無意間已經為人民共和國寫下了另一種歷史。王安憶又對她生長於斯的上海長期投注觀照,儼然成為上海敘事的代言人。而她歷經風格試驗,終究在現實主義裡發現歷久彌新的法則。
王安憶這些特色在新作《天香》裡有了更進一步的發揮。《天香》寫的還是上海,但這一回王安憶不再勾勒這座城市的現代或當代風貌,而是回到了上海的「史前」時代。她的故事始自嘉靖三十八年(1559),終於康熙六年(1667),講述上海仕紳家族的興衰命運,園林文化的窮奢極侈,還有這百年間一項由女性主導的工藝——刺繡——如何形成地方傳統。
王安憶是當代文壇的重量級作家,憑她的文名,多寫幾部招牌作《長恨歌》式的小說不是難事。但她陡然將創作背景拉到她並不熟悉的晚明,挑戰不可謂不大。也正因如此,她的用心值得我們注目。以下關於《天香》的介紹將著重三個層面:王安憶的個人上海「考古學」;她對現實主義的辯證;還有她所懷抱的小說創作美學。
王安憶對上海一往情深,九十年代中她開始鑽研這座城市的不同面貌。一部《長恨歌》寫盡上海從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浮華滄桑,也將自己推向海派文學傳人的位置。但王安憶顯然不願意只與韓邦慶、張愛玲呼應而已。她生長的時代讓她見識上海進入共和國後的起落;另一方面,她對上海浮出「現代」地表以前的身世也有無限好奇。她近年的作品,從《富萍》到《遍地梟雄》,從《啟蒙時代》到《月色撩人》,寫上海外來戶、小市民的浮沉經驗,也寫精英分子、有產階級的啼笑因緣。這些作品未必每本都擊中要害,但合而觀之,不能不令人感覺一種巴爾札克式的城市拼圖已經逐漸形成。
而一座偉大深邃的城市不能沒有過往的傳奇。有關上海在鴉片戰爭後崛起的種種我們已經耳熟能詳,王安憶要叩問的是:再以前呢?上海在宋代設鎮(1267),元代設縣(1290),歷經蛻變,到了有明一代已經成為中國棉紡重鎮,所在的松江地區甚至有了稅賦甲天下之說。
這是《天香》取材的大背景。王安憶著墨的是明代盛極而衰的那一刻。滬上子弟就算在科舉有所斬獲而致仕,也都早早辭官歸里。江南的聲色如此撩人,退出官場不為別的,只為了享受家鄉的一晌風流。小說裡的申家兄弟就是這樣的例子。他們打造天香園、種桃、制墨、養竹、疊石,四時節慶,忙得有聲有色。他們錦衣玉食,不事生產,因為消費——或浪費——就是生產。小說中段描寫申家老少「富」極無聊,刻意擺設店面,玩起買賣的遊戲,因此充滿諷刺。坐吃山空的日子畢竟有時而盡。等到家產敗光、無以為繼之時,當年女眷們藉以消磨時間的刺繡居然成為最後的營生手段。
王安憶記述申家園林始末,當然有更大的企圖。上海原是春申故里,《天香》以申為名,一開場就透露城市寓言的意義。如王所言,江南的城市裡,杭州歷史悠久,蘇州人文薈萃,比起來上海瞠乎其後。但這所都會力量呢另有獨特的精神面貌,在「器與道、物與我、動與止之間,無時不有現世的樂趣出現,填補著玄思冥想的空無。」上海雅俗兼備,魚龍混雜,什麼時候都能湊出一個「興興轟轟的小世界」。這個世界遠離北方政治紛擾,自有它消長的韻律。
從一般眼光來看,申家由絢爛而落魄,很可以作為一則警世寓言,坐實持盈保泰的教訓。如此王安憶似乎有意將明末的上海與當代的上海作對比,提醒我們這座城市前世與今生的微妙輪迴。但我以為王安憶的用心不僅止於此。她要寫出上海之所以為上海的潛規則,「軟實力」。當申家繁華散盡、後人流落到尋常百姓家後,他們所曾經浸潤其中的世故和機巧也同時滲入上海日常生活的肌理,千迴百轉,為下一輪的「太平盛世」作準備。
持盈保泰不是上海的本色。頹靡無罪,浮華有理,沒有了世世代代敗家散財的豪情壯舉,怎麼能造就日後五光十色?上海從來不按牌理出牌,並在矛盾中形成以現世為基準的時間觀。上海的歷史同時是反歷史。
這樣的讀法帶領我們進入《天香》的第二層意義,即王安憶的現實主義辯證。《天香》對申氏家族的描寫,舉凡園林遊冶,服裝器物,人情糾葛,都細膩得令人嘆為觀止。據此,讀者很難不以《金瓶梅》、《紅樓夢》以降的世情小說作對比。尤其《紅樓夢》有關簪纓世家樓起了、樓塌了的敘述,彷彿就是王安憶效法的對象。
但如果我們抱著悲金悼玉的期待來看《天香》,可能要失望了。因為整部小說雖不乏痴嗔悲歡的情節,敘事者的口吻卻顯得矜持而有距離。小說裡的人物橫跨四代,來來去去,彷彿與我們無親。如果《紅樓夢》動人來自於曹雪芹懺情與啟悟的力量,王安憶則另有所圖。她更關心的是一項名為江南家族的「物種」起滅,或更進一步,一種由此生出的「物質文化」——從園林到刺繡——的社會史意義。
由這個觀點來看,王安憶獨特的現實主義就呼之欲出。我們都記得《長恨歌》的主人翁王琦瑤一生與上海的命運相始終,多麼令人心有戚戚焉。但我們可能忽略了那樣的寫法其實是王安憶向以往風格的告別演出。《長恨歌》以後的作品抒情和感傷的氛圍淡去,代之以更多對個人和群體社會互動的白描和反思。中篇《富萍》應該是重要的轉捩點;王安憶返璞歸真,以謙卑的姿態觀察上海基層的生命作息。當中國文壇被後社會主義風潮吹得進退兩難之際,王安憶反其道而行。她重新審視現實主義所曾經示範的觀物知人的方法,還有更重要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投射的那種素樸清平的、物我相親 / 相忘的史觀。
《天香》的寫作是這一基礎的延伸。如王安憶自謂,她之寫作《天香》緣起於她對「顧繡」——上海地方繡藝的極致表現——歷史的好奇與追蹤。她對這項手工藝的「考古學」讓她得以敷衍出一則傳奇。就此,她的關懷落在傳統婦女勞作與創造互為因果的可能,刺繡作為一種物質工藝的發生與流傳,閨閣消閒文化轉型為平民生產文化的過程。
《天香》其實是反寫了《紅樓夢》以降世情小說的寫實觀。《天香》的結局沒有《紅樓夢》般的大痛苦、大悲憫;有的是大家閨秀洗盡鉛華後的安穩與平凡。傳奇不奇,過日子纔是硬道理。這是王安憶努力,不,勞動,的目標了。
然而《天香》是否也有另外一種寫實觀點呢?如上所述,王安憶的寫實又是以「興興轟轟」的上海浮世經驗為座標,她因此不能不碰觸社會主義唯物理想的對立面,就是上海城市物質史裡戀物、玩物——乃至於物化——的無窮誘惑。她在《天香》裡也不斷暗示,上海文化如果失去了踵事增華,標新立異的底蘊,也難以形成那樣豐富多變的庶民文化。名滿天下的「天香園繡」雖然起自市井,最後又歸向民間,但如果沒有上流社會女子的介入,以她們的蘭心慧手化俗為雅,就不足以形成日後的傳統。
寫作《天香》的王安憶似乎不能完全決定她的現實主義前提。她在後社會主義時代裡寫著前資本主義時代的故事,同時又投射著社會主義的緲緲鄉愁。循此我們要問,現實主義到底是作家還原所要描寫的世界,還是抽離出來,追溯現實的本質?是冷眼旁觀,還是物色緣情?是唯物論,還是微物論?更進一步,我們也要問上海的「真實」何嘗不來自它在「興興轟轟」中所哄抬出的,海市蜃樓般的,「不真實」或「超真實」?這是古老的問題,但它所呈現的兩難在《天香》裡顯得無比真切。
歸根結柢,寫實與寓言,紀實與虛構之間繁複對話關係從來就是王安憶創作關心的主題。這也是《天香》所可注意的第三個層面:這是一本關於創作的創作。早在一九九三年,王安憶就以小說《紀實與虛構》和盤托出她對小說創作的看法。小說為實虛構,但卻能以虛擊實,甚至滋生比現實更深刻的東西。
王安憶的說法也許是老生常談,要緊的是她如何落實她的信念。《紀實與虛構》的敘述兵分兩路,一路講女作家立足上海的寫作經驗,一路講女作家深入歷史、追蹤母系家族來龍去脈的過程。對王而言,每一次下筆都是與「虛構」亦步亦趨的糾纏,也是與「真實」短兵相接的碰撞。兩者之間互為表裡,最終形成的虛構也就是紀實。
寫《紀實與虛構》時期的王安憶仍然在意流行趨勢,不能免俗的採用後設小說模式。到了《天香》,她回歸嚴謹的古典現實主義敘事,切切實實的講述明代上海申家「天香園繡」從無到有的過程。但她其實要讓這現實主義筆法自行彰顯它的寓言面向。小說最重要的主題當然是刺繡,而刺繡最重要實踐者是女性。「天香園繡」起自偶然,終成營生需要;原是閨閣的寄託,卻被視為時尚的表徵;是高妙自足的藝術,也引出有形無形的身價。
就此王安憶筆鋒一轉,暗示女性與創作的關係,不也可以作如是觀?她於是不動聲色地重新編織出《紀實與虛構》裡的線索。小說如是寫道:
天香園繡可是以針線比筆墨,其實,與書畫同為一理。一是筆鋒,一是針尖,說到究竟,就是以一個描字,有過之而無有不及。(Ⅱ 50)
技藝這一樁事,可說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稍有不達,便無能無為;略有過,則入「雕蟲」末流……天香園繡與一般針黹有別,是因有詩書畫作底,所以……不讀書者不得繡!(Ⅲ 66)
這幾乎是王安憶的現身說法了。
王安憶佩服的同輩作家有信仰伊斯蘭教的張承志。張曾經苦於無法表達他對宗教最誠摯熱切的感受,幾經折磨,他寫出了《心靈史》,竟是以最冷靜的筆觸描寫伊斯蘭教的一支如何在極度困苦中保持高尚的志節,而且代代繁衍至今。王安憶指出,心靈是個極其抽象的概念,而「張承志卻找到了這樣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就是絕對的紀實。」「以最極端真實的材料去描寫最極端虛無的東西。」
王安憶在《紀實與虛構》的階段已經在思索張承志的心靈與形式的問題。但彼時她有話要說的衝動仍然太強,一直要到《天香》,她似乎才寫出了她的心靈史,「以最極端真實的材料去描寫最極端虛無的東西。」對她而言,「心靈」無他,就是思考她所謂「創造世界的方法」。
《天香》意圖提供海派精神的原初歷史造像,以及上海物質文明二律悖反的道理。這兩個層面最終必續納入作者個人的價值體系,成為她紀實與虛構的環節。在她寫作出版跨過三十年門檻的時刻,王安憶向三百年前天香園裡那些一針一線,埋首繡工的女性們致意。她明白寫作就像刺繡,就是一門手藝,但最精緻的手藝是可以巧奪天工的。從唯物寫唯心,從紀實寫虛構,王安憶一字一句參詳創作的真諦。是在這樣的勞作為,《天香》在王安憶的小說譜系裡有了獨特意義。
天漸漸冷下來,園子封了。宅子完工,章師傅帶了蕎麥阿毛回家,申府上冷清下來。小綢就帶著丫頭在屋裏,生一個炭盆,炭灰裏埋了花生、核桃、紅棗、白果,烤熟了,用長筷子搛在碗裏吃。時間在炭火的暖和糧食的香裏消磨著,往柯海回家的日子挨近。有時候,小桃和鎮海媳婦相邀來串門,帶了各自的孩子。阿奎五歲,阿昉只半歲,丫頭很是高興,要阿奎替她砸核桃,又要看嬸娘餵阿昉吃乳。與丫頭相反,小綢冷冷的,小桃以為嫌自己是姨娘,鎮海媳婦卻知道其實是對她。免不了的,要算計柯海的行程,鎮海媳婦說,無論如何,總是要回家過年。小桃說:倒不見得,維揚那種地方,處處留人!鎮海媳婦想攔沒攔住,小綢已經變臉:他愛回不回,我和丫頭兩個人就很好,我們向來喜歡清靜煩人多。話裏是嫌她們打擾的意思,這兩個走也不好,留也不好。只得另起話頭,議論妹妹的嫁娶,因正有新場的杜姓人家,託媒過來。杜家祖上中過進士,做過漕運監司的官,很慕申家的名聲。小綢就說:申家有什麼名聲?不過是顯富罷了,就是這一點叫人家看中,所以不顧正出庶出,只要嫁妝。話一出口冒犯兩頭,小桃是姨娘,阿奎便是庶出的身份;鎮海媳婦的嫁妝滬上出了名的,如此彷彿就只剩嫁妝,沒有人品,倒成了詬病。橫豎談不攏,串門的就要告辭。可丫頭正拉著阿昉的手,要將攥緊的拳頭攤開,看裏面藏著什麼。拳頭攤開,什麼也沒有,兩人都很意外,再將手翻過來看背面,還是沒有。大人們就靜靜地看孩子玩。下雪了,小綢終究憂鬱下來。柯海臨走那一夜寫的字,小綢收起來,又展開,等他回來親手裱。不由想起柯海調製漿糊的情景,那麼有興致,那麼有耐心。夜裏睡不著,打開妝奩,看那一塊塊的墨,看著看著,忽然嗅到了柯海的鼻息,呵在鬢邊,一驚。回頭看,房裏只有丫頭,伏在枕上酣睡。滿屋子的綾羅帳幔,都寫著柯海給起的字:綢!小綢念著自己的字,忽覺出一絲不祥,這“綢”可不是那“愁”?雪打在窗戶上,沙沙地響,響的都是“愁”字。早上起來,鴨四進套院裏鏟雪,說門前方濱成了一條雪溝,船走在溝裏,就好像在犁地。小綢不指望柯海回來了,可柯海偏就在這天夜裏回來。船走在太湖,天下起雪,船家再也不肯走,也雇不到車,都不捨得用馬。錢先生留下了,柯海一意要回家,結果乘了八人大轎,幾倍的轎錢,一路還要好酒好話哄著轎夫,走一程換一程地過來。黑天白地,只見一乘雪轎停在方濱申家碼頭,轎夫們齊聲大吼叫門。門叫開了,出來一串燈籠,映得雪地像著了火一般。轎裏面沒有一絲動靜,揭開雙重轎簾,裏面是一堆紅花綠葉的鄉下被窩,幾雙手上前去刨出一個人,睡得暖和和的,不知做什麼夢,睜開眼就叫了聲:小綢!夜裏,相擁著,小綢說:何苦呢?又是冰又是雪,一步不巧,滑到河裏餵魚!柯海就朝小綢身上拱一拱:吃吧,吃吧,你就是那條吃我的魚!小綢躲著他:哪個人要吃你!哪裡躲得開,柯海就像藤纏樹樣死纏著。小綢就說:既是如此,何不早幾日動身?柯海訴苦道:如何走得脫!阮郎的朋友多,都要見我們,一日恨不能排七餐宴。小綢不信:你們有那麼大面子!柯海道:並不是我們面子大,是阮郎面子大!小綢哼一聲,沒話了。柯海就將吃過的宴席在耳邊細數一遍,不外乎山珍海味,其中有兩樣稀奇是特別要說的。一是湯包,小碗大的一個,筷子夾起來,滿滿一兜湯在晃,一滴不漏,吃起來卻要十分在意,一不留神就燙了嘴;另一件說起來很普通,就是雞蛋,可要告訴端底,準得嚇一跳!小綢問怎麼了?一兩銀子一枚!柯海嚇人地說道,你知道為什麼?小綢愕然搖頭。那下蛋的母雞是用人參餵養的,所以雞蛋就有一股參的香,大補!小綢說:不如直接吃人參罷了,九曲十八彎,到頭還是一個參味。柯海只得解釋給她聽:好比你帶過來的墨,那一款紫草汁浸燈芯熏煙凝成的,泛朱紅的暗光,怎麼不說直接用紫草汁寫成字呢?小綢被他比得有些糊塗,轉不過來,又不服氣,翻個身說:千山萬水,拋家棄口去了數月,就長了吃的見識。柯海說:吃的見識也是見識,總比沒有的好。小綢說:好當然好,躲了清閒,不過,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不見得讓我和丫頭兩個搬屋子,等著你來住!柯海就說:我這麼苦趕,不就為了搬楠木樓,咱們住新樓,也好把院子騰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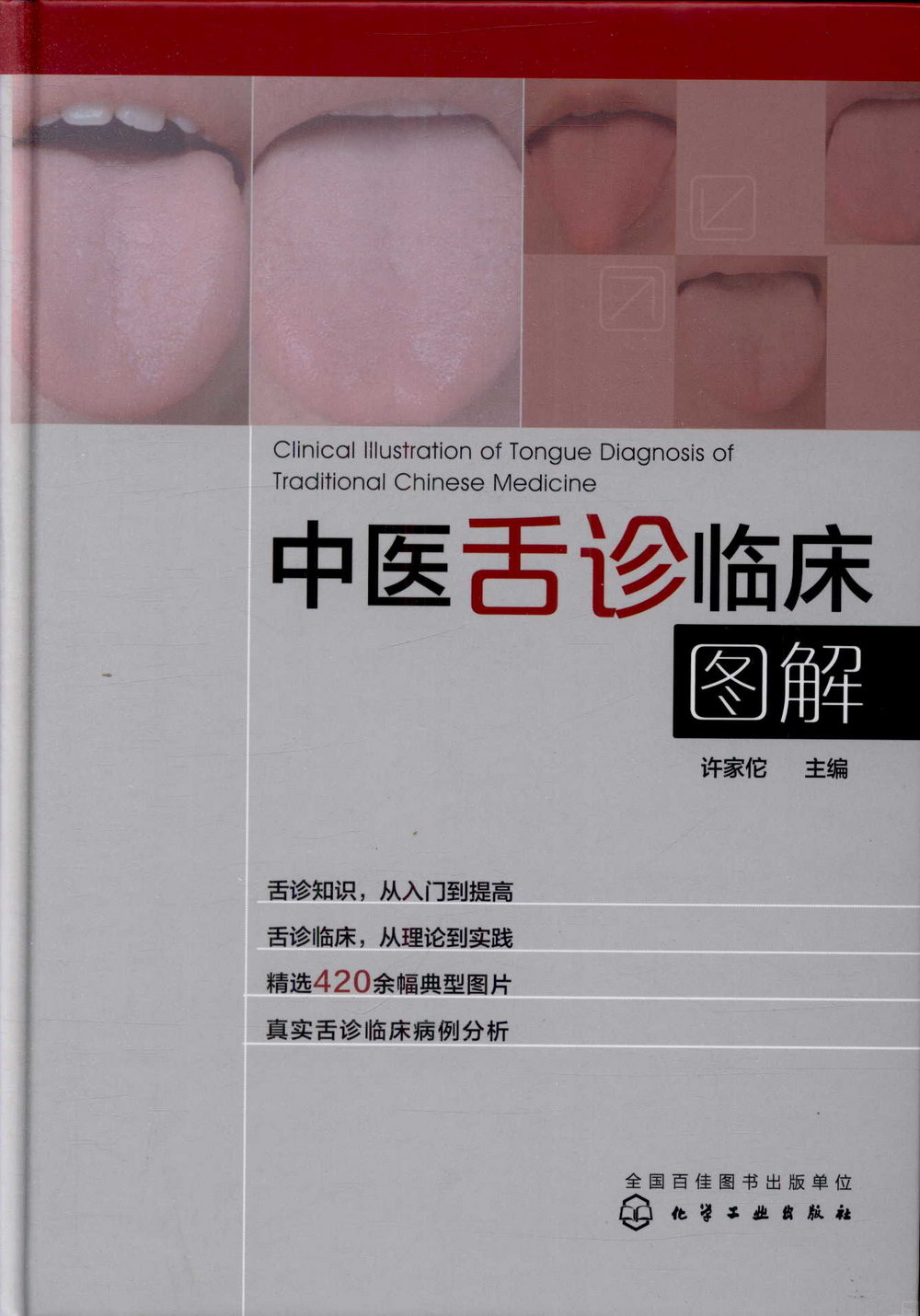 中醫舌診圖解
中醫舌診圖解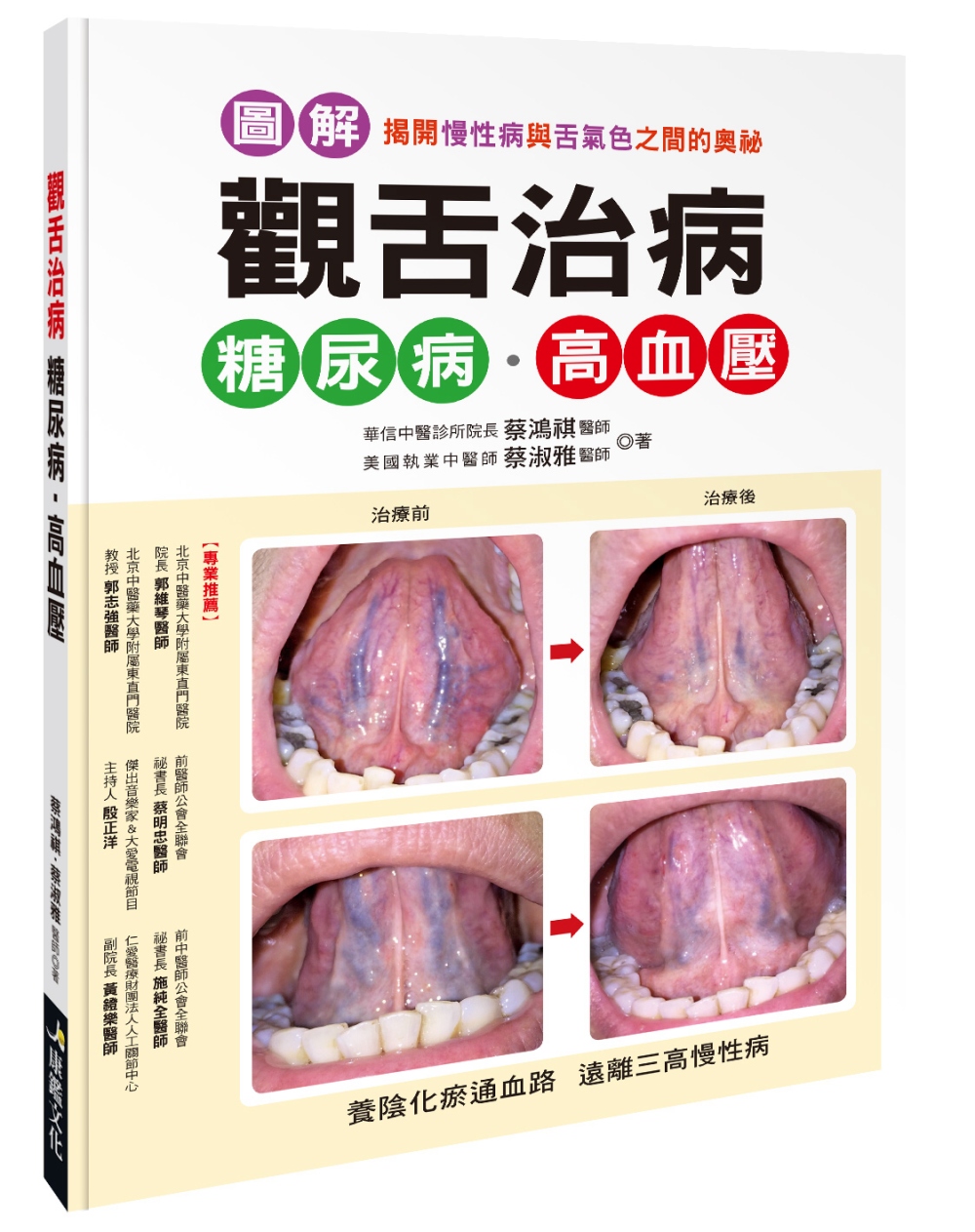 觀舌治病 糖尿病.高血壓:揭開慢性...
觀舌治病 糖尿病.高血壓:揭開慢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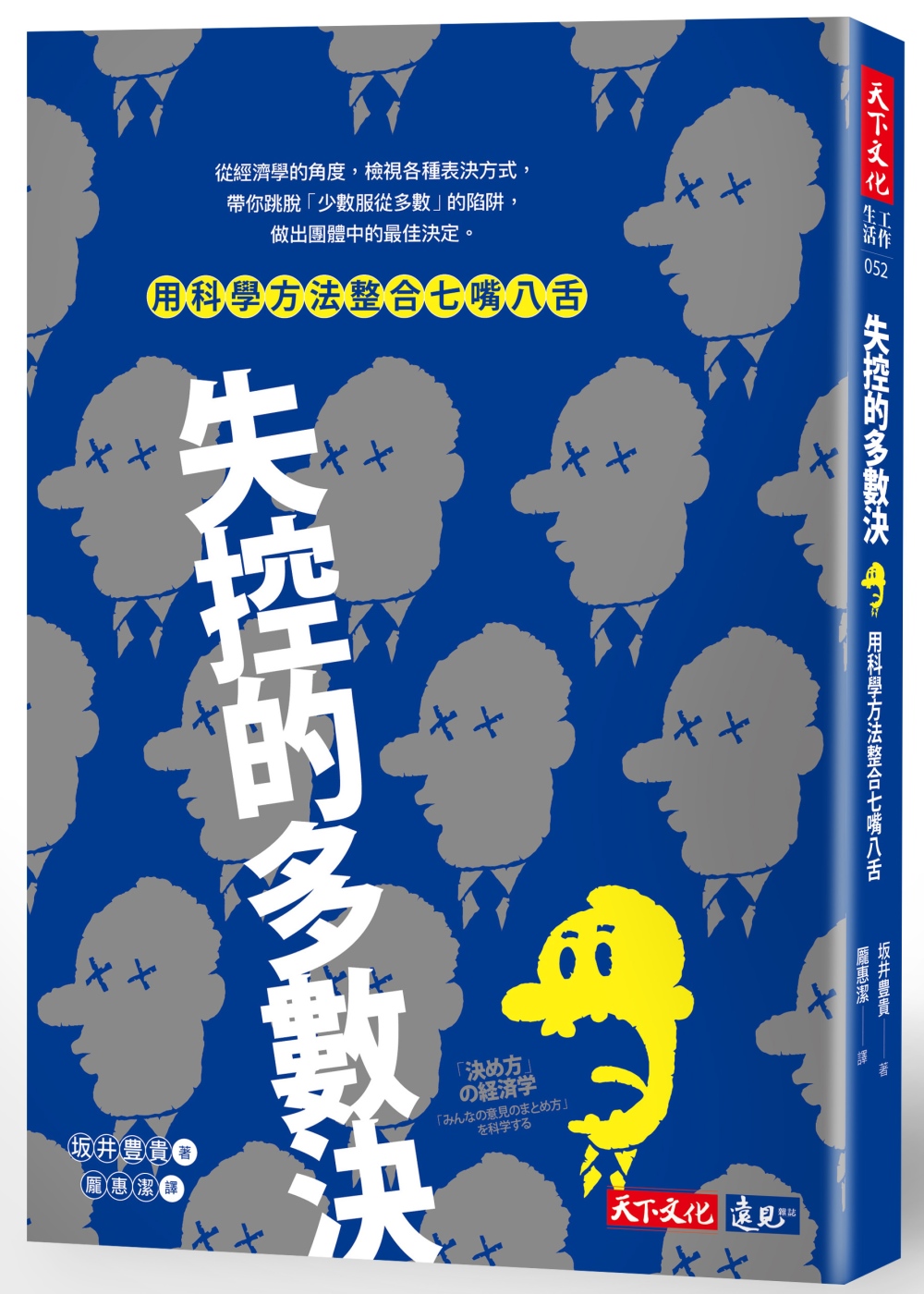 失控的多數決:用科學方法整合七嘴八舌
失控的多數決:用科學方法整合七嘴八舌 美的覺醒:蔣勳和你談眼、耳、鼻、舌、身
美的覺醒:蔣勳和你談眼、耳、鼻、舌、身 懷舊糕餅4:牛舌餅、老婆餅、脆皮流...
懷舊糕餅4:牛舌餅、老婆餅、脆皮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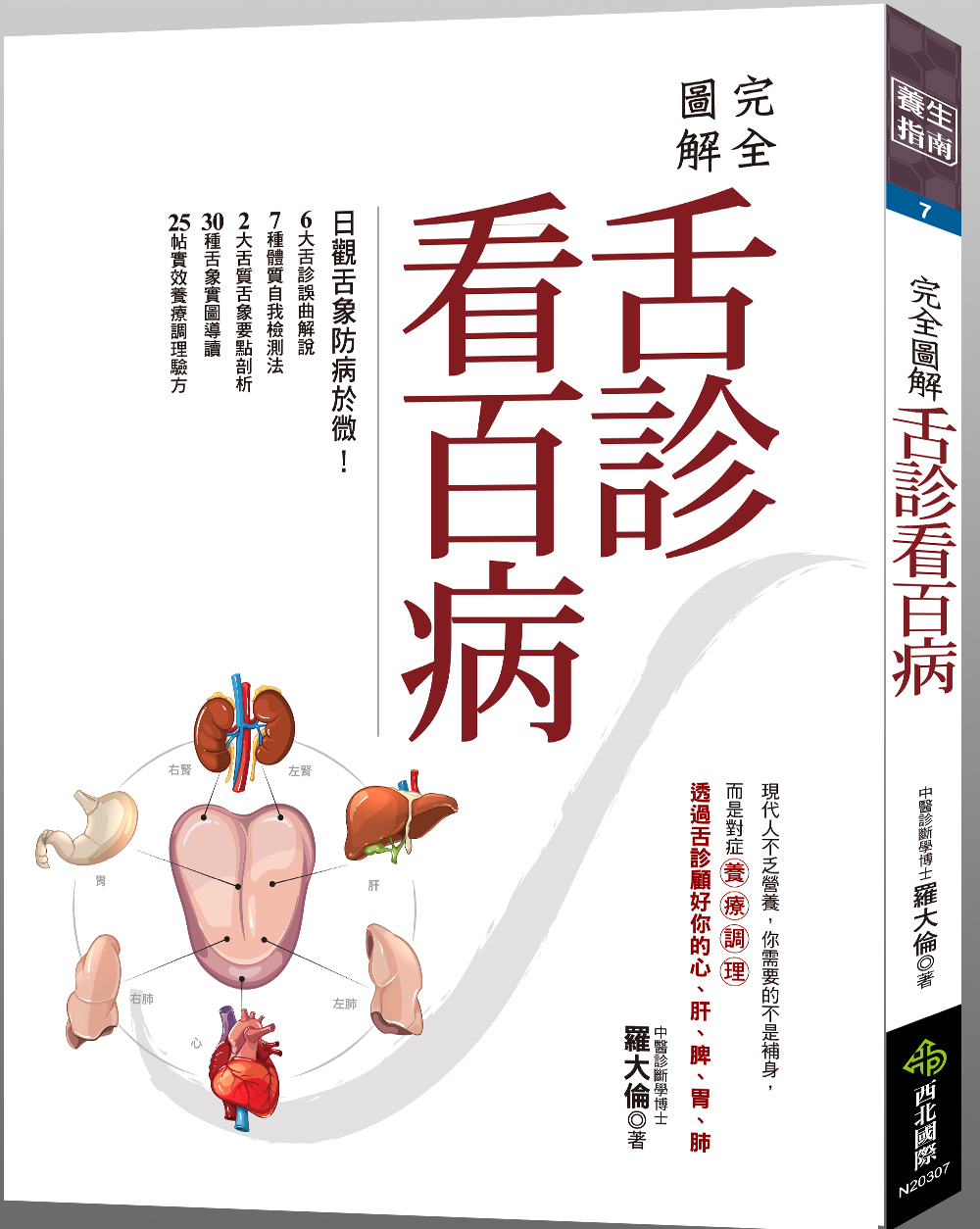 完全圖解:舌診看百病
完全圖解:舌診看百病 現代臨床望舌
現代臨床望舌 中國古醫籍整理叢書診法14:舌鑒辨正
中國古醫籍整理叢書診法14:舌鑒辨正 別傻了這才是仙台:烤牛舌‧杜之都‧...
別傻了這才是仙台:烤牛舌‧杜之都‧... 薩克斯風每日練習(貳):音色與運舌
薩克斯風每日練習(貳):音色與運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