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重新與世界連結 走出藍色深海 | 維持健康的好方法 - 2024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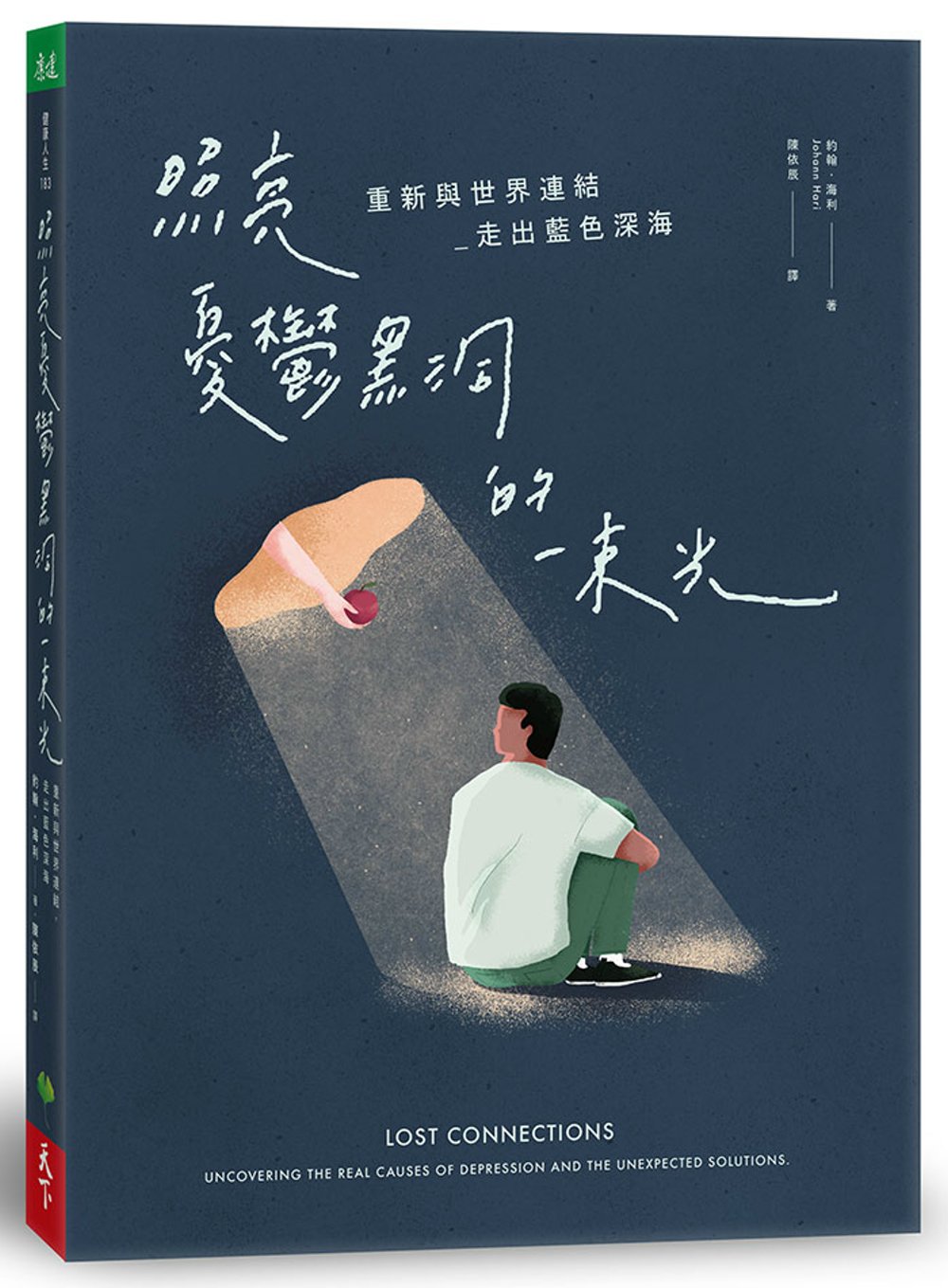
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重新與世界連結 走出藍色深海
英國亞馬遜4.5星、美國亞馬遜4星評價
解開憂鬱症之謎,找到了不需用藥的社會處方箋
TED Talk千萬人氣演講作家——英國記者約翰.海利
飛越千里探尋憂鬱症成因
「一本闡述為何沒有人應該被隔離在孤島上的細膩清晰的著作。無論你是有輕微的憂鬱症狀、或是嚴重到曾有輕生的念頭,如果你希望看到真實、且持續的改變,拿起這本書來讀,它可以提供你適當的指引。」——艾瑪.湯普遜(Emma Thompson,英國演員、奧斯卡影后)
18歲吞下人生第一顆抗憂鬱劑,到31歲停止吃藥為止的13年期間,約翰.海利一直相信醫生與醫學研究報告的說法:他的憂鬱症是因為大腦的血清素濃度不足,需要用藥來修復腦內失衡的化學狀態。
從個人用藥的親身經驗,他不完全贊同醫生的說法與抗憂鬱藥劑的效用。於是,秉著記者追根究柢的精神,他花了3年時間,旅行6000多公里,足跡遍及美國印第安那州的阿米希村、柏林科提公宅、巴西聖保羅、加拿大洛磯山脈、英國等地,深入採訪了社會科學家、精神科醫師、心理治療師、演化生物學家、社會運動人士、以及深受憂鬱症所苦的人,試圖找到造成憂鬱症的真正成因與解方。
約翰.海利在這趟旅程中一一解開心中長久以來的各種困惑,他發現,不能只歸咎於生理與心理因素,集體的社會因素——人際關係、價值觀、職場環境、創傷、對未來不抱希望等,才是造成憂鬱焦慮最主要的原因。
旅程結束後,他找到了對症處方:憂鬱症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全體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如果要減少這個造成人類社會整體疾病負擔第二名的憂鬱症的發生率,需仰賴社會群體的支持,進而與人、自然、有意義的價值觀、有意義的工作重新建立連結,克服自我成癮、童年創傷等,以及修復未來、建立信心。
作者說書與本書的採訪音檔,可上網觀看與聆聽:
www.thelostconnections.com
好評推薦
「這是一本會讓我更進一步修正治療策略的書,建議心理師和精神科醫師一定要仔細閱讀。」——林耕新(耕心療癒診所醫師、《解憂相談室》作者)
「嚴重困擾著美國社會的憂鬱與疏離的問題,《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一書提供了精彩、精闢的分析。」——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Rodham Clinton,美國民主黨政治人物)
「如果你曾經歷過情緒低落、感覺迷惘,這本書將改變你的生命……現在就讀吧!」——艾爾頓.強(Elton John,英國搖滾樂爵士)
「對於這個當代普及的問題,本書有非凡且細膩的新發現。筆法風趣、銳利,大膽、深入的分析推翻了過去我們對憂鬱症的認知。這本書引入了一股清新氣息,巧妙地挑戰當代正統的憂鬱症治療方法。」——馬克斯.潘伯頓(Max Pemberton,英國國民醫療保健服務中心心理醫師)
「這是一本具時代性、重要的、大膽又挑戰傳統觀點的讀物。現在是我們從單純藥物的角度轉向社會角度來檢視心理健康的時刻。這本書幫助我們這樣做。」——麥特.海格(Matt Haig,《我們住在焦慮星球》作者)
「這是你會推薦給你的好友,希望他們都能人手一本好好閱讀的精彩好書,因為裡面有太多令人省思、且你會想和他們一起討論的觀點。非常個人化的書寫,直率、幽默又謙遜,讓我讀得愛不釋手。」——布萊恩.依諾(Brian Eno,U2合唱團的唱片製作人)
「一本大膽又具啟發性的著作,對現代整體社會的幫助遠遠超過受憂鬱所苦的人。」——亞莉安娜.赫芬頓(Arianna Huffington,《赫芬頓郵報》創辦人)
許瑞云(花蓮慈濟醫院一般醫學內科醫師、《走出傷痛 破繭重生》作者)
作者簡介
約翰.海利(Johann Hari)
英國記者,生於1979年,2001年畢業於劍橋大學國王學院,主修社會學及政治學。他的採訪報導常見於歐美各主要媒體,包括《獨立報》、《紐約時報》、《世界報》、《衛報》、《洛杉磯時報》、《新共和》雜誌、《國家》雜誌等。23歲就獲選「英國記者協會年度記者」(Young Journalist of the Year at the British Press Awards ),兩度獲得國際特赦組織英國分會提名為「年度新聞記者」、獲選為英國報刊獎「年度文化評論員」(Cultural Commentator of the Year at the Comment Awards )等。
他在TED Talk的「你對上癮的認知都是錯的」(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Addiction Is Wrong)的影片觀看次數已經超過1000萬次。
著作:《追逐尖叫》(Chasing the Scream: The First and Last Days of the War on Drugs)
譯者簡介
陳依辰
專職中英文雙向筆譯
推薦序:
全觀面對憂鬱症,找到本源才能對症治療 林耕新(耕心療癒診所醫師、《解憂相談室》作者)
前言:蘋果
序:謎
Part I 破綻
第1章 魔法棒
第2章 失衡
第3章 哀傷排除條款
第4章 前無古人
Part II 脫節:憂鬱與焦慮的9大成因
第5章 後來有者(Part II前言)
第6章 原因一 與有意義的工作脫節
第7章 原因二 與他人脫節
第8章 原因三 與有意義的價值觀脫節
第9章 原因四 與童年創傷脫節
第10章 原因五 與階級和尊重脫節
第11章 原因六 與大自然脫節
第12章 原因七 與充滿希望和安全感的未來脫節
第13章 原因八和九 基因和大腦角色的變化
Part III 重新連結:另類抗憂鬱劑
第14章 牛
第15章 我們建了這座城市
第16章 重新與他人建立連結
第17章 「社交」處方
第18章 重新與有意義的工作建立連結
第19章 重新與有意義的價值觀建立連結
第20章 喜心,克服自我成癮
第21章 面對並克服童年創傷
第22章 修復未來
結論:回家
推薦序
全觀面對憂鬱症,找到本源才能對症治療
林耕新(耕心療癒診所醫師、《解憂相談室》作者)
老實說我有點後悔答應寫這篇序文,因為本書一定會衝擊很多同業對憂鬱症和抗憂鬱劑的既有想法,那就是「憂鬱症是大腦的疾病,更清楚一點說,腦內神經傳導物質不協調的結果,特別是血清素,因此,只要能調整好神經傳導物質,憂鬱症就能治癒。」這樣簡單的邏輯主導著目前國內外精神醫學界。
1990年代,百憂解(PROZAC)進入市場,藥廠行銷手法高明,聲稱只要你覺得稍微不快樂,百憂解能助你脫離痛苦,《神奇百憂解:改變性格的好幫手》(Listen to PROZAC)》還成了當年暢銷排行榜,作者甚至表示服用該藥後「比好還要好」,《時代》雜誌(TIME)第一次用藥丸當封面,全球為之瘋狂,認為憂鬱症將不再困擾人類,而事實是目前為止,坊間已有幾十種抗憂鬱劑,憂鬱症不只沒有減少,反而影響數億人口。
2004年5月,我到紐約參加第157屆全美精神醫學年會,討論主題是:「Dissolving The Mind-Brain Barrier」(溶化大腦與心靈之間的界限)主辦單位很特別邀請包頭巾的瑜伽大師談靜坐冥想對腦部的影響,隔壁講堂正討論著大腦血清素又發現最新的接受器,現場人山人海,我自己則是衝著精緻免費的早餐(藥廠贊助),無奈擠不進去只好到聽眾寥寥可數的瑜伽大師帶領大家冥想,很多醫師靜不下而相繼離去,搞得主辦單位也尷尬不已。
15年很快過去,人們對追求心靈的渴望不斷增加,很遺憾地,這並不包括精神醫學從業人員,據我的了解,大多數的精神科醫師被迫讓健保給付主導一切醫療行為,除了開藥以外已經不想、也不願投入非藥物的治療,特別是心理治療,而這個現象早就存在美國精神醫學界。
民眾自有區分辦法:開藥醫師和談話醫師,而他們說的談話醫師大部分還是指不能開藥的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和諮商心理師),如果病患只是要求開個藥,那就皆大歡喜,銀貨兩訖,迅速又有效率。萬一你想告訴醫師最近遇到的困擾或壓力,又不巧不是談話醫師,可能一句「多運動曬太陽,不要亂想」把你打發走。臨床上就遇過精神科醫師大喇喇地告訴個案:「我不會談的!」
筆走至此,讀者可能認為我反對藥物治療,支持20世紀末開始流行的新世紀(New Age)思想,一切靠心靈,開啟內心的能量……云云,甚至去附和更稀奇古怪毫無科學根據的療法,我要強調抗憂鬱劑之於憂鬱症是有其不可或缺的價值,在病症的初始治療階段,藥物仍是最有效而快速的途徑。根據整合分析(Pooled Met-Analysis)數百篇關於抗憂鬱劑療效的學術論文結果顯示,抗憂鬱劑的反應率(Response Rate,50%個案有效)大約45%到55%,也就是有高達45%到55%的病患對抗憂鬱劑的效果不佳或沒反應。
千萬要記得藥物絕對不是治療憂鬱症的唯一方法!
然而多數醫師隱瞞這項重大的事實,個案沒被告知:除了藥物治療以外,還有更多需要考慮的因素,透過作者到全世界遍訪學者專家調查後,列出憂鬱和焦慮的9大原因:
一、與有意義的工作脫節
二、與他人脫節
三、與有意義的價值觀脫節
四、與童年創傷脫節
五、與階級和尊重脱節
六、與大自然脫節
七、與充滿希望和安全感的未來脫節
八、與基因的變化
九 、與大腦角色的變化
數十年前,我們已經知道憂鬱症起因於生理—心理—社會三個因素影響,但心理和社會因素長期被刻意忽視而獨尊生理,這其中藥廠當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聯合國在2017年世界衛生日(World Health Day)的正式宣言中表示,主流生物醫學的敘事是基於偏見和選擇性使用研究結果,這會帶來弊大於利的影響,危害人們的健康權利,因此必須加以摒棄。」許多證據指向應該更深層地檢視憂鬱症起因,我們不應該——也絕對不行——用個人層次的改變來解決憂鬱和焦慮,解決與社會問題有密切關係的議題,將焦點從「化學失調」轉為「能力失調」。
我們錯誤地將解決憂鬱焦慮的責任全部交給病患,最多再加上醫師。憂鬱症成因複雜,解決之道也必須是整體的。生活及文化因素不可能置之事外,社會氛圍、政經情勢難道沒有影響?不過自己的認知行為狀態最重要,發展面對憂鬱症及抗憂鬱劑使用的正確認知,我相當同意作者面對自己的生病的態度,因為我也是這樣和憂鬱症病患分享:「你需要情緒低落的訊息,傾聽這個訊息,才會知道你遇到什麼問題,面對自己的弱點和痛苦,尊重疾病,甚至學習與疾病和平共存。」因此,個案會因為憂鬱症而獲得改變、成長,學會感謝疾病,這是終極治療目標。
最後,我想引用作者的結論:憂鬱症「在告訴我們,我們生活的方式出了問題。我們不能壓制或治這個標,必須要傾聽、尊重。只有當我們傾聽痛苦,才能跟著痛苦回到本源,也只有在本源,我們才能看出真正的原因,才能開始克服。」
讀完這本書,我只想說:「這是一本會讓我更進一步修正治療策略的書,建議心理師和精神科醫師一定要仔細閱讀。」
序
謎
我18歲時吞下人生第一顆抗憂鬱劑。那天,陽光微弱,我站在倫敦某購物中心藥局外頭。藥錠是白色的,小小一顆,吞下後會感受到一個化學的親吻。
那天早上,我去看醫生。我跟他說,我怎麼想也想不出有哪一天不想哭。打從小時候——在學校、大學、在家或跟朋友在一起時——我常必須抽離一下,把自己關起來哭。那種哭,不是滴個幾滴淚而已,而是踏踏實實地哭。即使沒掉淚,我心中仍不斷響起焦慮的獨白。我會自責:都在你腦裡。要跨過去。不要這麼懦弱。
這一切,讓我當時不好意思談起,現在也羞於敲鍵托出。
所有過來人談憂鬱或嚴重焦慮的書,都用了大篇幅書寫他們承受的磨難,深刻描述他們經歷的苦。在他人對憂鬱和嚴重焦慮不了解時,那類書籍是有其必要。多虧這些過來人打破了幾十年的禁忌,我現在不必再寫那樣的書,這本書也不是要談那樣的內容。我將現身說法,雖然真的很傷。
去看醫生的前一個月,我在巴塞隆納海邊,浪潮拍著我,我一面哭著。突然領悟到要如何解釋所發生的這一切,以及如何找到回去的路。當時是夏天,我跟朋友的歐洲旅行來到中段,之後我會成為我們家第一個上好大學的人。我們買了便宜的學生周遊火車券,一個月內在歐洲搭火車都不必再付費。旅途上,我們睡的是青年旅館。我想像著黃色沙灘和精緻文化——如羅浮宮、大麻菸捲、火辣好看的義大利人。出發前,我才被人生第一個愛上的人拒絕。我可以感受到我的情緒從身體流洩出來,好似讓人尷尬的體味。
旅行未如我所計畫的那樣。我在威尼斯的貢多拉船上大哭。在馬特洪峰上大叫。在布拉格卡夫卡的屋子裡發抖。
對我來說,這不尋常,但也沒那麼不尋常。我的人生,有些片刻就像那樣,痛苦無法控制,我想從這個世界消失。在巴塞隆納時,我止不住地哭,朋友說:「多數人不會這樣,你知道吧?」
然後,我經歷了人生少數靈光乍現的片刻。我對著她說:「我很憂鬱!並不是我想太多。我不是不開心,也不是脆弱——只是憂鬱!」
聽起來很奇怪,說出口的當下,我竟有種快感,像在沙發後面意外找到一疊錢一樣。有個詞是用來形容那種感覺的,那是一種病症,就像糖尿病、腸躁症這種專有名詞。我已經聽了好幾年,這會兒終於懂了。他們說的就是我!我突然想到憂鬱有解——抗憂鬱藥物。那正是我需要的!一回家我會去拿藥,有了藥就能回歸正常,所有不憂鬱的一面也能得到解放。我總會有些跟憂鬱無關的衝動,想去接觸人、學點東西、想認識世界。那一部分的我終會擺脫束縛,而且很快。
隔天,我們到巴塞隆納市中心的奎爾公園(Park Güell)。那是建築師高第(Antoni Gaudí)的作品,設計極為奇異,所有東西不成比例,像走進哈哈鏡一般。一會兒,你會走入一個隧道,裡面的東西如漣漪般排列,猶如被波浪打過。一會兒,龍飛竄到波浪狀鋼材建築上,活靈活現的。一切的一切都不像真實世界應有的樣貌。我一邊逛,一面想:我腦袋裡就是這樣子,混亂、錯誤。但這一切很快會搞定!
所有靈光乍現的片刻看似倏忽,但其實蘊釀已久。我是知道憂鬱症的,我在肥皂劇中看過,也在書中讀過。我聽過母親談論憂鬱和焦慮,見過她為了這些症狀吃藥。我知道解藥是什麼,早在幾年前,全世界媒體都在吹擂。我十幾歲的那些年正是百憂解(Prozac)的時代——那是新藥物的曙光,第一次有藥物宣稱能治療憂鬱症,而且沒有副作用。那十年中,有暢銷書說這藥物的確會讓人「好上加好」,服用後會比正常人還要強壯健康。
這些說法我照單全收,從不曾停下來想過。1990年代末的那幾年,關於百憂解的討論很多,到處可見。我想,應該我也適用。
去看醫生的那天下午,天晴氣朗。我的醫生對這一切也深信不疑。在小小的診間裡,他耐心跟我說明為何我會有這些感覺。他說有些人先天大腦血清素濃度不足,造成憂鬱症——也就是異常、持續而脫序的不開心狀態,久久不散。幸好,就在我成年時,「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SSRIs,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問世,這類藥物能修復血清素濃度到正常水準。醫生說,憂鬱症是一種腦疾,解藥就在這裡。他還拿出大腦圖跟我講解。
他說憂鬱其實跟大腦有關,只是型態不同。憂鬱不是想像出來的,憂鬱真實而具體,起因於大腦功能失常。
他其實也不用多說,那套說法我早就信服。不到十分鐘,我就帶著克憂果(Seroxat,在美國名為Paxil)的處方箋離開了。
過沒幾年,在我寫這本書的同時,有人向我指出那天醫生沒提出的所有問題:有沒有什麼原因可能讓你這麼憂鬱?是否遇到了什麼事情?有沒有什麼事對你造成了傷害,而你會想去改變的呢?其實,就算當時醫生有問這些問題,我大概也答不出來。我猜我會兩眼無神地看著他。然後,我可能會說:我過得很好。我是有些狀況沒錯,但沒道理不開心,而且是這麼不開心。
不管怎樣,他沒問,我也沒多想。之後的13年,醫生都是開這種藥給我,從來也沒問過那些問題。要是問了,我想我會發火,並且回他:「腦子都壞了,無法製造能帶來快樂的化學物質,何必問呢?不嫌殘忍嗎?你不會問失智者把鑰匙放到哪裡去吧。這問題很瞎,你是沒讀過醫學院嗎?」
醫生告訴我要兩週才會看到藥效,但就在我領藥的那晚,我感受到一股暖流在體內流竄,一種輕柔的彈弄,我確定那是我大腦突觸發出聲音,進入正確設定。我躺在床上,聽著自己錄的、聽到快爛掉的精選錄音帶,我知道,接下來很久的時間,我都不會再哭泣。
幾週後,我離家到大學報到,帶著新的防禦武器——藥物,我不擔心。在學校,我是抗憂鬱藥物的福音傳教士。每當朋友覺得難過時,我會給他們一些藥試試看,跟他們說可以去跟醫生拿一些。我相信我的狀態不只是「不憂鬱」而已,而是更好更棒!我告訴自己,我有超強修復力和活力。沒錯,藥物帶來有感的副作用,我胖很多、也超會流汗,但那只是小小代價。我周遭的朋友再也不必受苦,而且你看,我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但是,才幾個月我就發現,哀傷有時會無預警地回過頭來找我,無法解釋,毫無道理可循。最後只好求助醫生,我們決定提高劑量。我從一天20毫克提高到一天30毫克,從原本的白藥丸變成藍藥丸。
接近20歲的那幾年和整個二字頭就靠這樣過去了。我向人宣傳這些藥物的優點。又過了一段時間,悲傷再次湧現,醫生給我更高的劑量,從30變成40毫克,再從40變成50。最後,我一天得吃兩顆藍色藥丸,也就是60毫克。我一次比一次胖,越來越容易流汗,但我知道,這個代價是值得的。
如果有人問,我會跟他們解釋憂鬱症是大腦疾病,解藥是「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後來當了記者,我在報上撰文對大眾耐心說明。我將持續回流的悲傷解釋成治療過程的必經之路——大腦裡的化學物質會用盡,無法控制也無從了解。我會說謝天謝地,藥物很有效。看看我,我就是實例。雖然腦袋裡三不五時會質疑,但只要多吞一兩顆藥,疑問就快速拋在腦後。
我自有一套說帖。其實我現在知道,這個說帖分兩部分。首先是憂鬱症病因——大腦失能,血清素濃度不足或大腦硬體出了亂子。第二是解藥,也就是藥物,藥物會修復腦內化學狀態。
我喜歡這個說帖。這說帖對我來說是合理的,也引領著我的生活。
~~~~~~
關於這些憂鬱感從何而來,我只聽過一個不同的可能說法,而且不是醫生說的,而是書上看來的,電視上也有人討論過。他們說憂鬱和焦慮跟基因有關。我知道我母親在我出生前(和出生後)都很抑鬱和焦慮。家族內本來就有這些問題,時間可以回溯到更早。這些對我來說是兩種平行的說法,但兩者都表示——憂鬱和焦慮是與生俱來的,就在血肉裡。
~~~~~~
三年前我開始寫這本書,因為我還是有些謎題沒有解開。那些謎,是我長期信服的那一套所無法解釋的,我想找出答案。
來談第一個謎。服藥了幾年後,某天我坐在診間,向治療師訴說我感激抗憂鬱藥物的存在,讓我快活。他說,「怪了,我看你還是憂鬱呀。」我不懂他的意思。他繼續說,「你常常都是憂鬱的。在我看來,跟你服藥前的描述沒有差太多。」
我耐心跟他說明那是他有所不知——憂鬱症是血清素不足所引起,所以我要提高血清素濃度。我心想:「這些治療師到底受過什麼訓練了?」
這些年,他不時會溫和地提出這一點。他說,提高劑量就會迎刃而解的想法與事實不符,因為我多數時間還是心情低落,充滿著憂鬱和焦慮。我不想聽他的說法,心中除了生氣,也覺得此人淺陋。
過了好幾年,我終於聽懂他當時說的話。到了30歲出頭,我突然了解,那時在巴塞隆納沙灘上的頓悟是錯的。因為,吃再怎麼高的劑量,抗憂鬱藥物都壓不住我的悲傷。一開始,化學製劑確實有明顯的緩和效果,但當那個防護泡泡散去,刺痛的不愉悅感會再度回來。強烈的念頭不斷出現,說著人生了無目的,所做的一切不具意義,只是浪費時間。焦慮感揮之不去。
因此,我想了解的第一個謎是:為何服用抗憂鬱藥物還是會憂鬱?我樣樣做對了,卻還是有些不對勁,原因何在?
~~~~~~
過去幾十年來,有件怪事發生在我家。
打從小時候,我就有印象廚房桌上有好幾個藥罐,上面有我看不懂的白色標籤。我寫過家中有藥物成癮的問題,以及在我非常久遠的記憶裡我曾努力要搖醒親戚,但沒有成功。幼年時,主宰我們的生活並不是禁藥,而是醫生開的藥——舊款抗憂鬱劑和鎮定劑,如煩寧錠(Valium)。有了化學物質幫我們微調,日子才過得下去。
我說的怪事是,隨著我的成長過程,西方文明在用藥這件事情上,追上了我們家。小時候跟朋友在一起時,我發現別人家並不會照三餐吃藥。沒有人用藥物來鎮定、鼓舞或對抗憂鬱。我才知道,原來我家的狀況並不尋常。
慢慢地,隨著時間推移,藥物在日常生活中越來越稀鬆平常,不管是醫生開的、經核可的或建議服用的藥物。時至今日,藥物處處可見。在美國,每五位成人就有一人因心理問題服用至少一種藥物;中年婦女更有近四分之一服用過抗憂鬱藥物;約有一成男高中生服用有助於專心的強效藥物。合法和非法藥物的成癮問題極為普遍,致使美國白人男性壽命首次在昇平時期下降。這些影響已擴散到整個西方世界。舉例來說,在你閱讀到這裡的時候,法國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服用合法精神異常藥物(如抗憂鬱藥),而英國可說是全歐洲用量最兇的。抗憂鬱藥物幾乎讓你無所遁逃——科學家在西方國家的自來水中發現抗憂鬱藥劑成分,因為抗憂鬱藥物的服用者眾,排放後又無法從日常飲用水中過濾。確實,到處都充斥著這些藥物。
昔日異事今已司空見慣。人們也沒有多討論,就接受了周遭很多人得用強效藥物對抗憂鬱,以正常過日。
我第二個疑惑是:怎麼會多出這麼多明顯感覺憂鬱和嚴重焦慮的人呢?是有什麼改變嗎?
~~~~~~
31歲是我成年後第一次完全不吃藥。治療師的溫柔提醒——我雖然持續服藥,卻仍覺得憂鬱——我聽而不聞了10年。一直到人生遇到危機,無法甩開壞心情,我決定要聽他的。為什麼我努力了這麼久,卻好像沒用?我把手上最後一包克憂果沖進馬桶,覺得我心頭的疑問像月台上等待接送的小孩,等待著我去注意。我為何依然憂鬱呢?為什麼這麼多人跟我一樣?
然後,我又發現第三個謎團:除了腦內化學物質失調外,有無其他原因會導致憂鬱焦慮呢?如果有,那會是什麼?
我當然還是不想探究。關於痛苦,一旦你接受了某套說法,就不願再去質疑。就好像用韁繩套住憂鬱,就覺得可以控制憂鬱一樣。我擔心,萬一推翻了與我共存許久的說法,那痛苦會像脫韁動物,反過來奴役我。
曾有好幾年的時間,每當我開始研究這些謎題,看科學報告、和這些報告的作者對話,我就會退縮。因為他們說的事讓我亂了陣腳,使我更焦慮。我在我的著作《追逐尖叫:橫跨9國、1000個日子的追蹤,找到成癮的根源,以及失控也能重來的人生》(Chasing the Scream: The First and Last Days of the War on Drugs)有討論這部分。聽起來可能有點扯,我覺得訪問墨西哥毒梟殺手比調查憂鬱和焦慮的起因容易,推翻我用來解釋我的情緒、感受和這些感受從何而來的說帖,對我而言是一種危險。
終於,我決定停止視而不見。於是花了三年,旅行四千多英哩,在世界各地做了200次以上的訪問,對象是全球最重要的社會科學家、歷經憂鬱和焦慮幽谷的人、痊癒者。我去了許多本來想都沒想過的地方,如印第安那州的阿米希村(Amish village)、柏林一個勇敢抗爭的公宅社區、巴西某個禁止廣告的城市,以及位於巴爾的摩、運用創新方法帶領人們回溯創傷的實驗室。這些見聞讓我重新修正我的見解——對於我自己、對於蔓延在我們文化中的悲傷。
~~~~~~
本書一開始,我想提一下決定本書用語的兩件事。這兩件事對我來說都很意外。
我的醫生說我同時有憂鬱症和嚴重焦慮。我一直相信這兩者獨立不相關。在我因為這兩種病症求診的13年間,相關討論也是這麼認為。但在我研究的同時,我注意到一件怪事:所有助長憂鬱的因素也會使焦慮惡化,反之亦然,也就是兩者同步消長。
這個發現有點意思。當我在加拿大和心理學教授羅伯.科倫貝格(Robert Kohlenberg)談時我才開始了解。羅伯也曾一度認為憂鬱和焦慮是兩件獨立的事,但他從20多年的研究中發現——數據顯示這兩者並非各自獨立。實務上,「特別是憂鬱症和焦慮,診斷時會重疊」。有時,其中一個會比另一個明顯。例如這個月比較焦慮,而下個月比較常哭。但把這兩者視為彼此無關並類比成肺炎和斷腿的關係,則是沒有根據的。羅伯已證明這當中的關聯還「很含糊未清」。
羅伯的論點在科學討論中得到支持。近年來,美國主要資助醫學研究的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已不再贊助將憂鬱症和焦慮症視為不同診斷的研究。羅伯說:「他們希望看到更務實,更能反映臨床實務的研究。」
我開始將憂鬱和焦慮視為同一首歌的不同唱片封面,由兩個樂團個別演出。憂鬱症是強拍情緒搖滾樂團的版本,而焦慮是嘶吼重金屬樂團的版本,兩者用的是同一套樂譜——就是長得不像的雙胞胎。
~~~~~~
當我研究這9個憂鬱和焦慮的起因時,我又有其他發現。過去,只要寫憂鬱和焦慮的文章,我會開宗明義地說:我不是在談不快樂。「不快樂」和「憂鬱」天差地遠。對憂鬱者來說,最火大就是有人叫你振作、開心一點,或教你開心的方法,彷彿你只是最近生活不順遂。這就像叫斷腿的人去跳舞作樂。
我一面研究這些證據,一面又看到一件不能忽略的事。
會加重憂鬱和焦慮的因素也會讓人不開心。不開心和憂鬱間有某種連結存在,但兩者還是非常不同,就像因車禍失去一根手指跟失去一條手臂、仆街和墜落懸崖,都是不同但有關聯的事件。我逐漸明白,憂鬱和焦慮像矛最尖銳的邊緣,刺入我們文化中絕大多數的人。因此,本書的諸多內容,就算非憂鬱或嚴重焦慮者也會覺得認同。
~~~~~~
建議讀者閱讀本書時,一邊查閱注解中的科學研究,並跟我一樣帶著懷疑態度看待這些研究。提出質疑,看看是否有破綻。有什麼誤解,代價都會很高。而我自己都開始相信我本來會震驚的事。
大環境長期誤導我們對憂鬱和焦慮的認識。
對於自己的憂鬱,我信過兩套說法。18歲之前,我認為憂鬱存在「在大腦裡」,也就是不真實、是想像虛構的、一種自我沉溺、不自在、某種弱點。之後的13年,「在大腦裡」對我來說已有不同的意義——大腦運作失常。
後來我明白這兩種說法都不對。使憂鬱和焦慮惡化的主因與大腦無關,而絕大部分跟外在世界及生活方式有關。我找到至少9個已證明會造成憂鬱和焦慮的因素,過去沒有人像這樣一口氣提出,其中幾項越來越明顯,使我們每況愈下。
對我來說,這是一段艱辛旅程。讀者會發現,我曾堅信的「憂鬱症起因於大腦失常」在過程中逐漸崩解,那是我捍衛過的觀念,曾有好長一段時間,我拒絕面對別人給我看的反證。接受新想法並不像鑽進溫暖被窩那般舒適,而是一場戰役。
只是,如果將就長期的錯誤,只會繼續困著並惡化。探詢憂鬱和焦慮的原因一開始讓人卻步,因為那些原因藏在文化的深處。我感到畏懼,但在前進的過程中,我知道盡頭會有真正的解藥。
當我終於了解我和許多同病相憐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時,我知道真正的解藥正等待著我們。那些解藥,不是公認沒效果的化學藥劑,也不是要花錢買或口服的產品,但它們掌握著離苦之道的源頭。
 絕望筆記:風靡芬蘭的負面情緒釋放手冊
絕望筆記:風靡芬蘭的負面情緒釋放手冊 整理情緒背包,激發前進的勇氣:情緒...
整理情緒背包,激發前進的勇氣:情緒... 情緒密碼:釋放受困情緒的奇效療法
情緒密碼:釋放受困情緒的奇效療法 絕望筆記:風靡芬蘭的負面情緒釋放手冊
絕望筆記:風靡芬蘭的負面情緒釋放手冊 按壓手穴道,釋放壞情緒
按壓手穴道,釋放壞情緒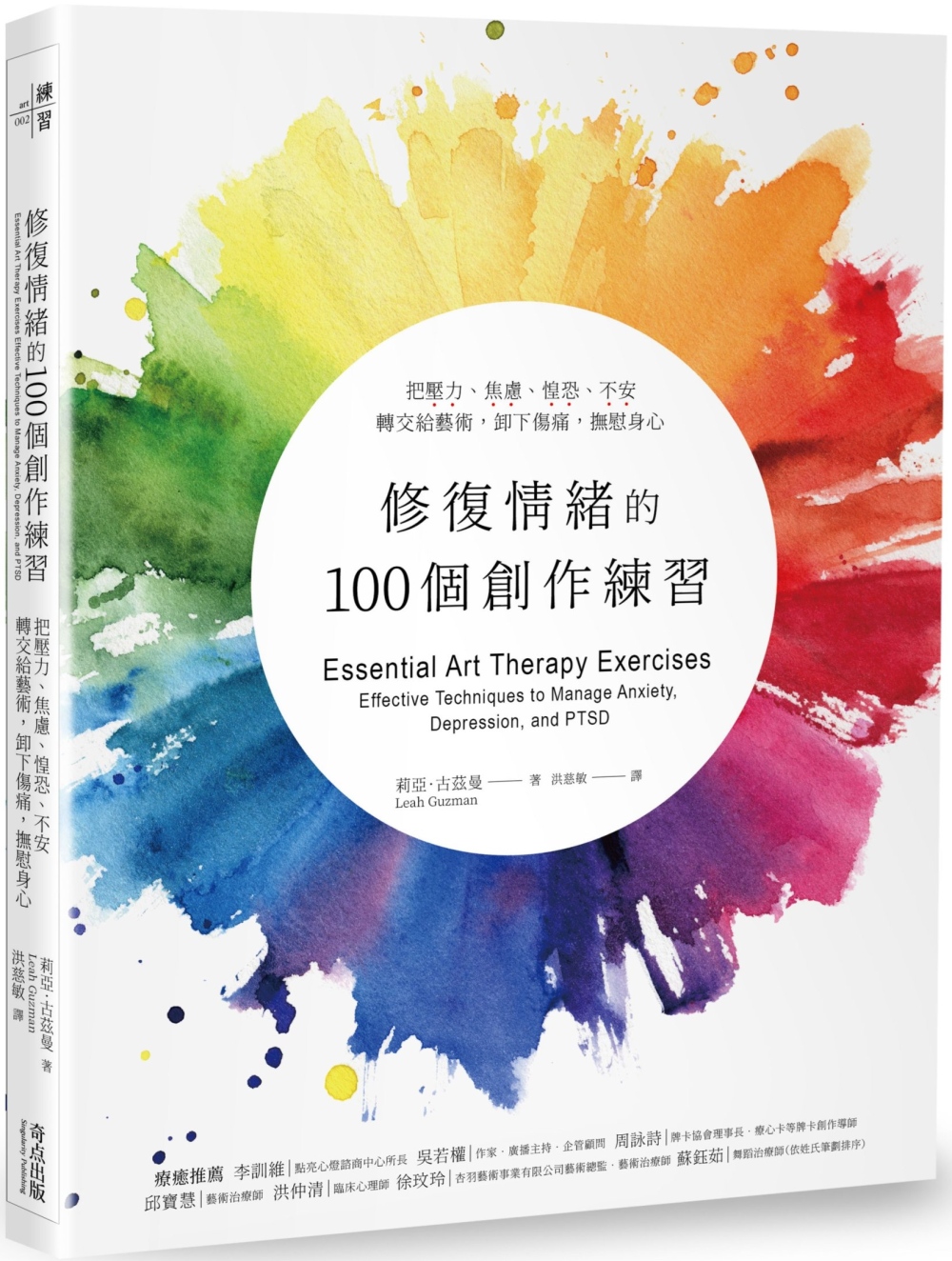 修復情緒的100個創作練習:把壓力...
修復情緒的100個創作練習:把壓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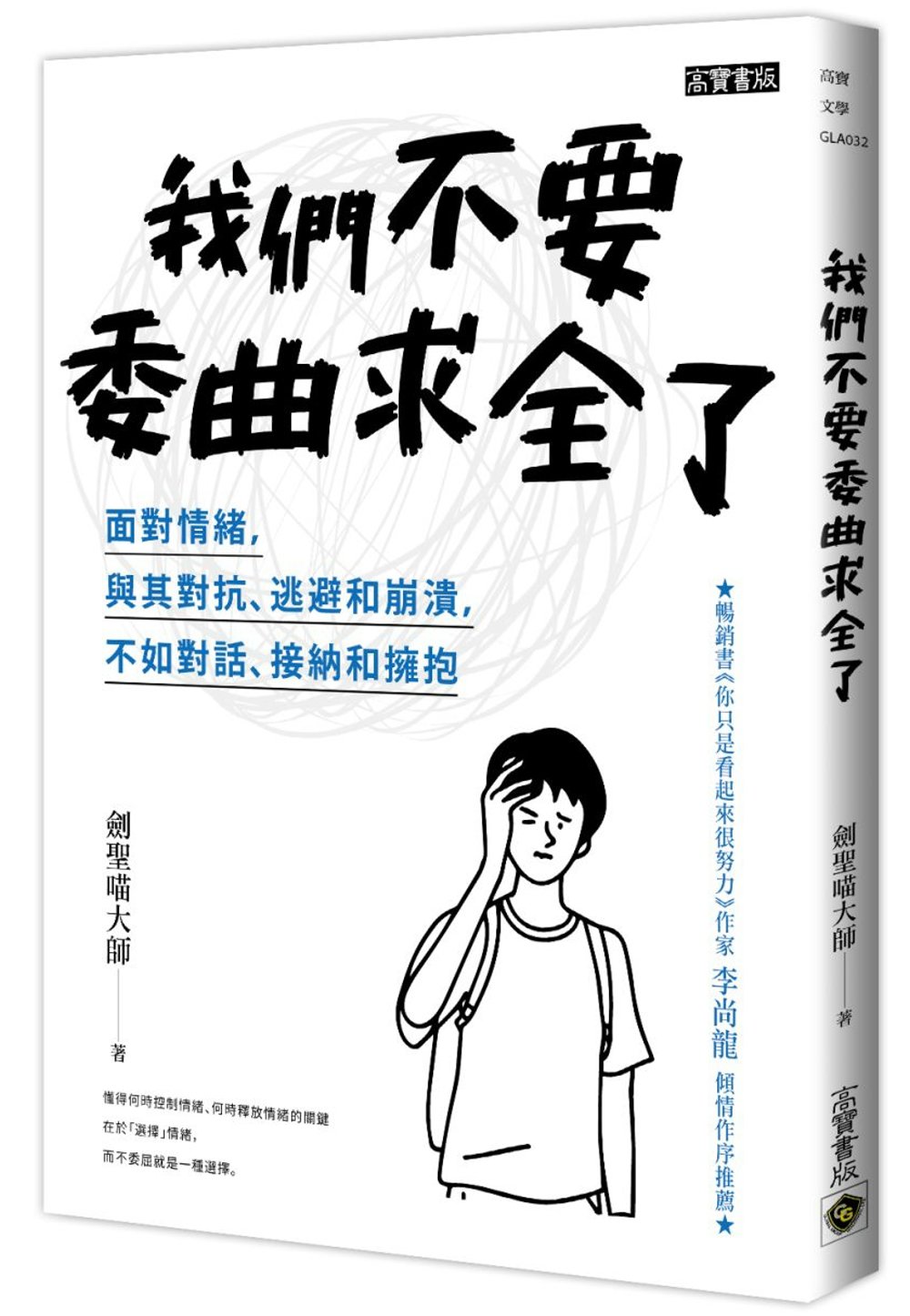 我們不要委曲求全了:面對情緒,與其...
我們不要委曲求全了:面對情緒,與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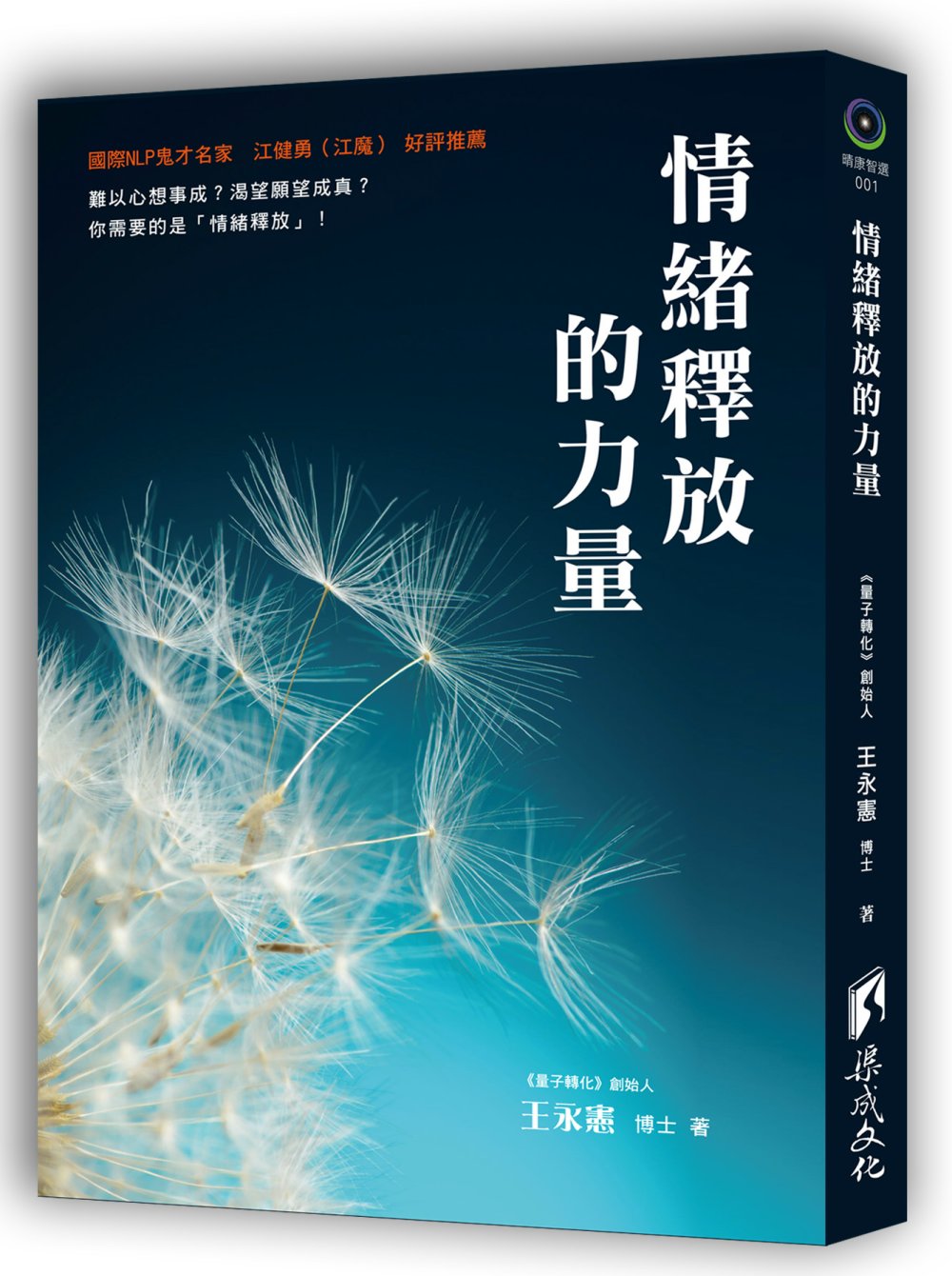 情緒釋放的力量
情緒釋放的力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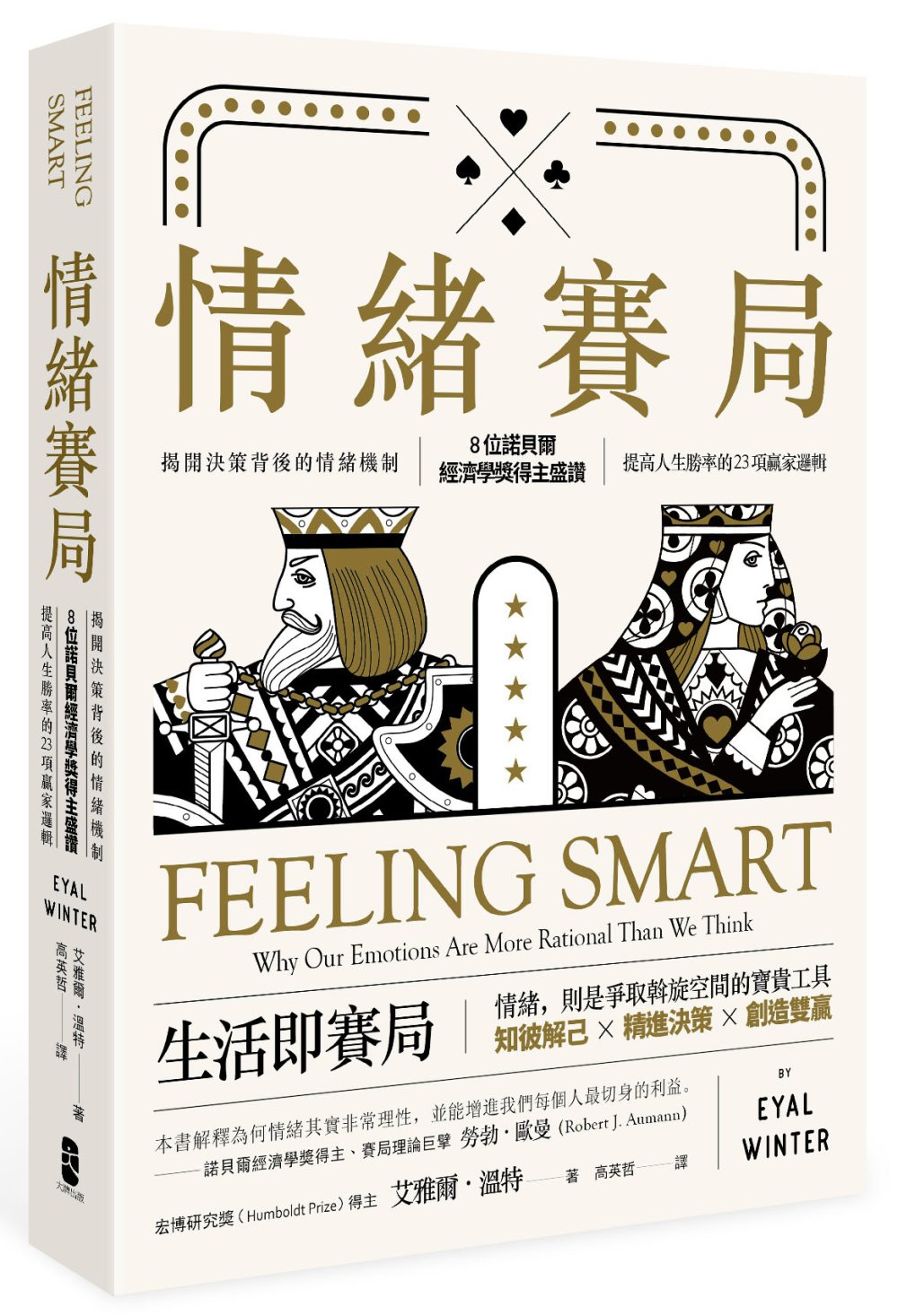 情緒賽局:揭開決策背後的情緒機制,...
情緒賽局:揭開決策背後的情緒機制,... 不只是憂鬱:心理治療師教你面對情緒...
不只是憂鬱:心理治療師教你面對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