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囚的最後時刻:我在美國最惡名昭彰的監獄擔任死刑見證人的那段日子 | 維持健康的好方法 - 2024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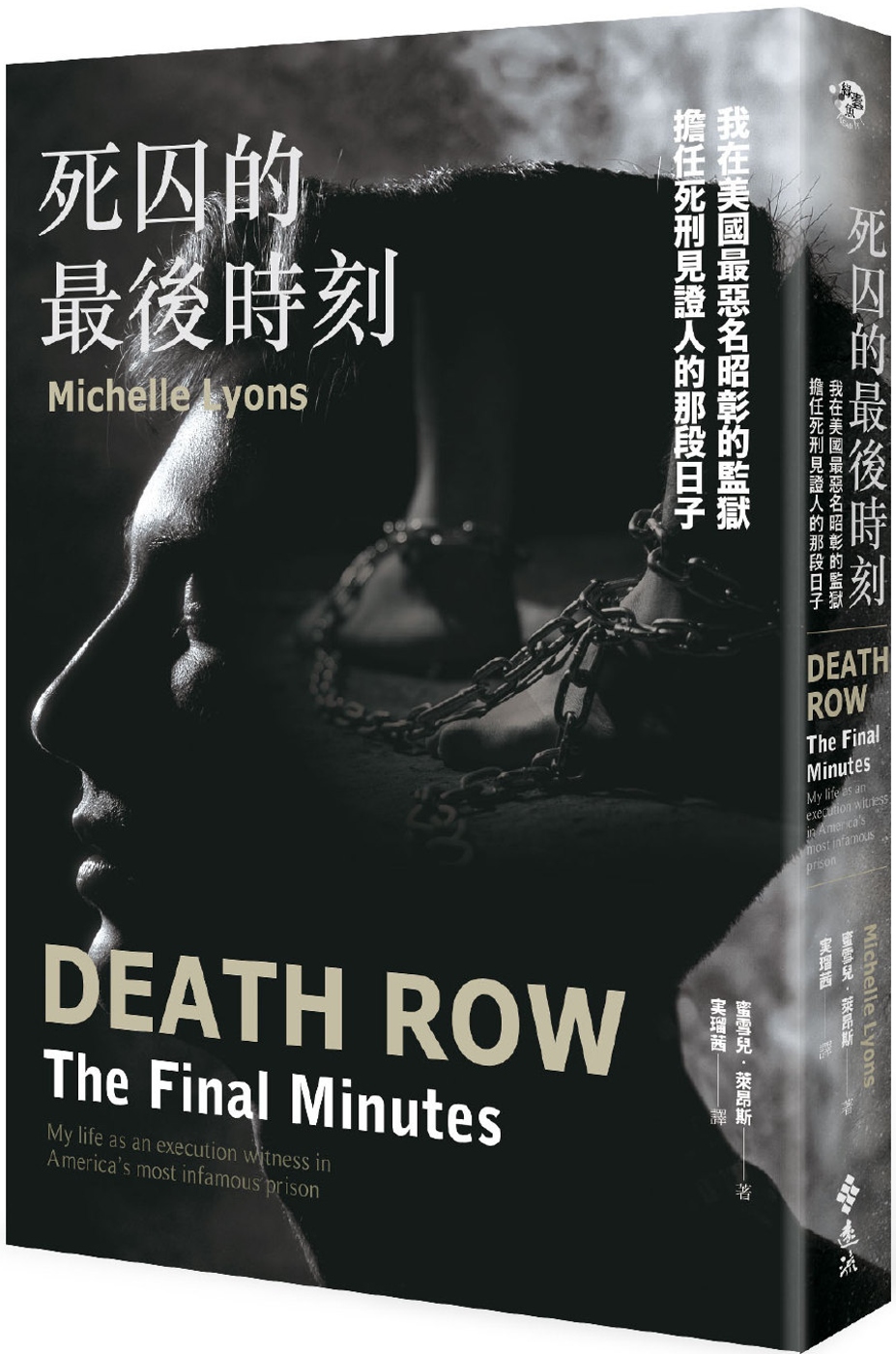
死囚的最後時刻:我在美國最惡名昭彰的監獄擔任死刑見證人的那段日子
12年來,蜜雪兒親眼見證了近300起死刑執行
關於罪與罰的思辨,這是一份絕對不可略過的證言
■一個目睹死刑的罕見經歷,見證與反思死刑制度的第一手資料。
■一本揉合感性(記者觀點)與理性(制度面執行弊端)的報導文學。
■本書不在探討「反對」或「支持」死刑,而是透過真實故事來思考生命的意義與本質。
我不知道罪犯被處決,是否有讓任何事變得更好?
他的死是否為被害人家屬帶來平靜?正義是否得以伸張?
又或者,在死刑之前,我們全都成了受害者?
亨茨維爾小鎮是個非常特別的地方。它的風景如畫,也是德州司法部的監獄所在,尤其以關押死刑犯聞名,被歐洲媒體稱作「世界死刑之都」。小鎮裡共有七間監獄,城鎮因而圍繞著監獄而發展,監獄體系也成了該市最大的雇主,鎮民多數於監獄就業,本書作者蜜雪兒‧萊昂斯也不例外。1998年,她22歲,以地方媒體身分首度進入監獄報導死刑過程。那時,她覺得受刑人不過是睡著了,相較於被鐵槌擊殺的兩位老人,正義也未免過於失衡。
之後三年,她在目睹死刑執行過程42回之後,蜜雪兒‧萊昂斯積累了在電視上侃侃而談死刑現場的經驗,受聘為德州司法部公關室發言人兼死刑驗證官。十二年內,她親眼驗證近300位死刑犯的生命終結,依法一一記錄死刑現場,近身觀察與探索關於死刑的制度與生命的本質。
起初,基於媒體記者的客觀與專業,蜜雪兒‧萊昂斯還能冷靜地扮演法制上的旁觀者。隨著目睹死刑次數的增加,她心中的疑慮開始浮現出來。她逐漸認識並喜歡某些死刑犯,看著他們死去,嚴密的心防終於敵不住死囚眼角的淚珠與其母親的心碎。成為死刑驗證官(同時成為母親)的她,開始對死刑本質提出質疑──處決犯人是否反而讓我們全都成了受害者?
難得的是,已退休的前任驗證官及公關室主任賴瑞‧費茲傑羅,以共同見識過多起死刑的退役者身分,於本書中回顧了這凡人罕至的歷程,共同探索死刑裁罰的本質。對於死刑存廢爭議,透過作者的第一手記錄,以及個人生命經驗的轉變,無疑是一份不可略過的證言。
誠摯推薦
朱宥勳│作家
李茂生│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林立青│作家
黃益中│公民教師、《思辨》作者
黃致豪│律師,司法心理學研究者
楊貴智│律師,法律白話文運動站長
▶如果你暫時沒有太多心思或動力去細細思索「死刑」這個問題,就試著讓本書作者帶著你看看這些死刑犯吧──看看他們如何生,如何死,看看一個近距離的死刑相關工作者心念的艱難。雖然遠在千里之外,作者萊昂斯針對這些在美國德州的死刑犯的描述,對死刑制度的觀察,以及自己所面對的思想困境,栩栩如生。
然後,我們或許可以坐下來聊聊死刑是不是正義,或者,怎麼樣的死刑算是一種正義──如果真的有人知道何謂單純的正義的話。──黃致豪│執業律師、司法心理學研究者
▶這本書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它並非單純支持或反對死刑,而是以回顧這些事件對於自身的改變。這也是一本罕見的揉合感性(第一人稱的記者觀點)與理性(提出制度面及執行弊端)的報導文學,相信這麼獨特的經歷更能引起讀者們以前所未見的觀點,思考刑罰制度與生命本質的重大議題。
對於台灣社會來說,談論死刑或許過於早熟,因為我們都還沒能認識死刑的樣貌,就要思考死刑的意義,因此不論你支持死刑或反對死刑,都建議透過這本書一窺死刑的真實樣貌(即使抱持著偷窺刑場的八卦心態),必定將會讓我們對死刑有更多不同的看法。──楊貴智│律師、法律白話文運動站長
好評推薦
■Amazon五星評價節錄:
▶這是一個很好的閱讀體驗。可以藉機瞭解一些最嚴重的罪犯和處理這些罪犯的人。而且,蜜雪兒讓我們知道目睹到數百次的執行後,會怎麼改變一個人。
▶作者並沒有試圖改變任何人看待死刑的立場,但她成功的為讀者了提供充足思考面向。這不是非黑即白的簡單問題,也不僅僅是政治言論或抗議海報上的口號。無論您是贊成或反對死刑,都會從一個親眼目睹死刑執行逾300次的人身上,獲得發人深省的新見解。
▶多年來我讀過的最好的書之一。我哭了,我笑了;我思索並驚嘆於這本回憶錄提及的尊嚴、恩典、友誼和全方位的愛的展現。
「讀完有種惆悵縈繞心頭,讓人低迴不已。」——《休士頓紀事報》(Houston Chronicle)
作者簡介
蜜雪兒‧萊昂斯(Michelle Lyons)
蜜雪兒‧萊昂斯在成為德州刑事司法部發言人之前是一名監獄記者。在12年中,她目睹了德州近300起最臭名昭著的死刑犯的處決,並在離開司法部的公職之後,決定把這個悲傷歷程記錄下來。
譯者簡介
実瑠茜
政大英語系畢業(日文輔系),曾任職出版社英、日文編輯多年,喜歡鑽研語言文字與異國文化,目前為自由譯者。
推薦序
讓我們來談談死刑──黃致豪(執業律師、司法心理學研究者)
看見死刑的樣貌──楊貴智(律師、法律白話文運動站長)
作者的話
序章 一滴眼淚
第1章 慢慢地睡去
第2章 這只是一份工作
第3章 站在岔路口
第4章 這就是賴瑞
第5章 好日子永遠不會結束
第6章 一個奇怪的人
第7章 你再看一次
第8章 或許這樣才能不再痛苦
第9章 一個可怕的地方
第10章 有點憂鬱
第11章 我偷走了時間
第12章 情緒傾瀉而出
第13章 悲傷不是某個人的專利
第14章 沒有陽光的日子
結語 記得他是我的職責?
致謝辭
序
一滴眼淚
我不記得他的名字、罪行,或是他在德州哪個郡落網,但他的輪廓卻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裡,就像他昨天才剛被處決一樣。他是一名邁入中年的黑人,有著長長的下巴,看起來有些自傲。然而,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一無所有。沒有家人,沒有朋友,沒有安慰他的人。也許他不希望他們來看他,也許他們並不在意,也許他根本就沒有家人或朋友。沒有人見證他的死。至少我是這麼記得的。
也許他們感到恐懼,也許他們無法負擔這趟旅程的費用,也許因為犯罪年代久遠,執法當局無法找到任何和他有關聯的人。不管原因是什麼,當時只有一名典獄官、兩名記者(包含我在內)透過玻璃看著這個男人;他被牢牢地綁在輪床上,兩隻手臂都插著針頭,雙眼死盯著天花板看。
這個男人並沒有往旁邊看。他為什麼要這麼做?觀刑室裡沒有任何一個他認識的人。但是他應該有注意到,典獄長站在他的頭部附近,牧師的手則是放在他的膝蓋下方。當典獄長走上前去,問他是否有遺言要交代時,他只是搖了搖頭,沒有說任何話。接著,他開始眨起眼來。這時我注意到,他的右眼眼角有一滴眼淚。他拚命想把這滴眼淚眨掉,不想讓我們看見。它在那裡打轉了一會兒,然後從他的臉頰滑落。這景象深深地撼動了我,實在無法用言語形容。
典獄長打了個暗號,化學藥劑開始流進他的體內。他咳了幾下,並從喉嚨裡發出呼嚕聲,接著吐出最後一口氣。一位醫生走進了行刑室,宣告這個男人已經死亡,並且在他的頭上蓋上白布。
因為我還可以看見他的臉,我大可翻閱我手裡的文件,弄清楚他是誰。但是,我不想記住他的名字、他犯了什麼罪,或者這件事是在哪裡發生的。這一切都不重要。我記得他被處決的過程,這樣就夠了。在我有生之年,我再也不會看到像他這麼孤單且被人遺忘的人了。
當我看著男男女女在德州的行刑室裡死去(一開始是以記者的身分,後來則是作為監獄體系的一員),我不允許自己進一步省思。當我翻閱我早年的行刑筆記時,發現某些事困擾著我。然而,我當時因為年輕、無所畏懼,以為凡事只有黑白兩面。 只要有任何疑慮,我都把它們埋藏在內心深處的某個角落。如果我開始探索,目睹死刑讓我有什麼樣的感覺,或是開始想太多,我要怎麼再踏進那個房間,月復一月、年復一年?
若是我哭了,我該怎麼辦?若是有人察覺我臉上的恐懼,又該怎麼辦?我不能讓這種事發生。我故作麻木,這麼做保護了我,使我能夠繼續下去。然而,我總是迅速地將心中的疑慮塞進那個角落,對它們置之不理,於是最後越塞越滿。
直到我離開監獄體系,在十一年內目睹了至少兩百八十次死刑之後,我才開始仔細思考自己看過的這些事。我會突然看見裝盛在咖啡色大型塑膠容器裡的水果酒,這是獄方為了牢房裡的死刑犯所準備的。或者我會在打開一包洋芋片時聞到行刑室的氣味,或是在收聽電台時,想起我和死刑犯在他被處決前幾小時的對話。我的腦海中會浮現出他們的身影:在輪床上含著一滴眼淚的男人,或是殺童兇手瑞奇‧麥金恩(Ricky McGinn)的母親。
儘管麥金恩太太衰老虛弱,只能靠輪椅行動,她還是盛裝打扮——小碎花洋裝配上珍珠項鍊,前來見證兒子的死。當麥金恩要交代遺言時,她掙扎著從輪椅上站起來,用她佈滿皺紋的雙手按壓著觀刑室的玻璃,因為她想確保他在踏上黃泉路之前能夠看到她。
當我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晚上經常會躲在被窩裡哭泣,因為我意識到所有愛我的人終將死去。直到現在,我依然可以看見我臥房的淡綠色牆壁,並且聽見樓下電視的聲音。我會打開收音機,希望音樂聲可以消除我對死亡的想法。我會從房門口望向走廊上昏暗的燈光,我的眼淚順著臉頰流了下來。但是我從來沒想過要下樓,把我心中的恐懼告訴父母親。這一直是我心裡的祕密。當我們死去之後,我們都會在天堂裡團聚。這樣想會讓我好過一點。如果死亡並非失去,為什麼要害怕親人先行離開呢?我們都會再相聚,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隨著年齡漸長,我對死亡的恐懼演變成害怕被人遺忘。我責怪高中時的初戀情人。當我跟隨家人從德州搬到伊利諾州時,我們分手了。然後在幾個星期之內,他就和別人交往了。我感到傷心欲絕。很顯然,我沒有自己想的那麼重要。雖然聽起來很傻,但這件事困擾了我很多年。每當一段關係結束時,我都會想:「我是否對他們有影響力?他們會記得我嗎?」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希望在我死後,骨灰可以撒在某個美麗的地方。一塊小石頭擺在乏人問津的地方,沒有什麼比這更悲傷的了。孤獨且被人遺忘,就如同這個男人,我不記得他的名字,也不記得他犯了什麼罪。
推薦序
讓我們來談談死刑
黃致豪(執業律師、司法心理學研究者)
有時,我不禁要感謝台灣近乎全然密行的死刑執行制度—至少這樣的制度讓我可以無需憂慮何時必須直面當事人的執行,只要在被告知執行時,無力的躲在辦公桌後狂飲或痛哭(或兼而有之),就可以了。
作為一介寧可隱姓埋名的死刑與重案辯護律師,不,這次我並不想談論廢除死刑的問題。相反的,我想談談死刑的存在這件事。
更直接了當的說,我想談談「承認並面對」死刑的存在這件事。
在台灣,死刑是刑法第33條明定的五種主刑之一。換句話說,死刑這種刑罰的形式上合法性,其實無庸置疑。因此,有關廢除死刑這件事的思考,在台灣多半僅止於倡議與辯論層次。既然說是「倡議與辯論」,那麼它在思維活動以及公共政策思辯等層面,也就是相對單純的紙(或口)上談兵:列舉優缺點,找出相關數據,成本效益分析,本國與外國刑事政策分析……等。總之,正反雙方動動嘴皮,談談情感,試圖說服對方(或指控對方愚昧);彷彿一場論辯過後,世界就會得到救贖,人性就能重歸樸真。無怪乎,大家總愛透過支持或反對死刑,來建構自我的正義感或道德觀。
事情似乎總是那麼簡單,那麼直觀,直到,除非,你真的近距離面對過死刑。
如果你近距離面對過死刑,你就可能了解死刑之重,死刑之難以承受。而我指的近距離,必須是真正、第一手的近距離—不是那些端坐在法檯上、廟堂裡、辦公室內,好整以暇、夸夸而論為何被告該死或不該死的法律人或立法者,而是那些必須在日常工作當中實際面對死刑與死刑犯的人,那些死刑辯護律師,以及監所矯正與執行人員。
那些有機會看到死刑犯仍然具備屬於人的一面的人。
當你有機會看到這一面時,哪怕我們根本不去討論死刑存廢,你恐怕也很難不去針對現行的死刑執行制度,提出許多疑問。雖說死刑在台灣「形式上」合法性無庸置疑,但是實質上的合法性呢?制度上也都良好無缺嗎?似乎又未必如此。
相較於本書作者蜜雪兒・萊昂斯(Michelle Lyons)本其見聞所揭露的美國死刑狀況與內情,台灣本土的死刑執行方式以及死刑犯的處遇,顯然也有不少值得深入思考之處。舉幾個例子:
▶判處死刑定讞之後,依照法務部「審核死刑案件執行實施要點」(不是法律,是一種行政規則,也就是僅供行政機關自己參考的規範)核決執行的小組,是怎麼運作的?有哪些人員參與?有哪些決定的具體標準?真的有經過實質討論嗎?這些討論不能讓外界知道嗎?理由為何?
▶死刑執行的對象(這一次誰該死),是如何選出來的?樂透嗎?順序嗎?還是依照法務部長(或行政院長?或總統?)的心情?
▶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的人,有被排除在死刑執行之外(刑事訴訟法第465條)嗎?誰來判斷有沒有精神障礙呢?
▶死刑犯的案件是否有祕密證人不可靠,律師辯護不力,檢警偵訊不當,或者鑑識證據有問題的狀況?誰來決定有無問題?
▶為什麼死刑執行,沒有確定的日期?
▶為什麼死刑執行不能通知家屬、被害者家屬與辯護人,讓他們有機會見最後一面?
▶死刑犯不定期限被關押在死囚牢中,日日面對「今天會不會就是執行日」的恐懼(監獄行刑法第91條),會不會造成另一種特殊的折磨嗎?這種折磨,是法律設計的原意嗎?
▶死刑犯或其家屬在不知道何時執行的狀況下,該如何依照赦免法(全文僅八條,完全沒提到該如何提出赦免請求)向總統提出赦免的請求呢?
▶死刑犯在監的處遇,跟一般收容人有什麼不一樣之處?這樣的差別,是合法的嗎?
以上的種種問題,我或許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從台灣的法律與制度當中,我始終得不到答案。透過本書作者的見聞,我卻再次確認了死刑的艱難。
要國家動手殺人很簡單—只要人民一直對政府不滿,或許很快國家就會動手轉移大家的注意力了。但作為一種政策制度,死刑極度艱難—尤其是,如果你真的有機會直接面對,也願意深入思索此一議題的話。
如果你暫時沒有太多心思或動力去細細思索這個問題,就試著讓本書作者帶著你看看這些死刑犯吧—看看他們如何生,如何死,看看一個近距離的死刑相關工作者心念的艱難。雖然遠在千里之外,作者萊昂斯針對這些在美國德州的死刑犯的描述,以及對死刑制度的觀察,以及自己所面對的思想困境,栩栩如生。
然後,我們或許可以坐下來聊聊死刑是不是正義,或者,怎麼樣的死刑算是一種正義—如果真的有人知道何謂單純的正義的話。
看見死刑的樣貌
楊貴智(律師、法律白話文運動站長)
曾經有人提出一道有趣的思想實驗:一位永遠看不見紅色的色盲,透過自己的努力學習了大量與紅色的知識,例如紅色是人類可見光譜中長波末端的顏色,波長大約為630到750奈米等,那這個人到底能不能宣稱自己真正認識紅色?死刑議題也有類似困境,太多人辯論死刑存廢,卻鮮有人真正看過死刑,因此我們到底能不能宣稱自己真正認識死刑?
在台灣,除了檢察官以及法警外,其他人沒有機會目睹死刑執行的過程,即使是媒體也只能大批守候在監獄外,用麥克風捕捉奪取人犯生命的「槍響」來填飽社會大眾對於「正義」的欲求。相反地,不知道這算是幸運還是不幸,這本書的作者蜜雪兒‧萊昂斯(Michelle Lyons)得以記者身分親身目睹三百起死刑執行,甚至在死刑犯漫長等待「用盡救濟程序」的日子裡,能有機會親身接近死刑犯並與她們互動,因此有別於其他從理論出發的文獻書籍,這些經歷讓本書帶我們看見死刑真實樣貌,因此特別與眾不同。
我高中的時候參加辯論社,「我國刑法是否應廢除死刑?」可說是這一段青春最好的註腳,從我入社開始一路到參加全國性辯論盃這道經典辯題反覆成為賽題。對於一個小辯士來說,閱讀刑法以及犯罪學教科書,學習威嚇、應報、再教育以及兩害相權取其輕等等學說,從抽象的理論建構精緻的辯詞是贏得比賽的巧門,但總讓我有雙腳踏不著地面的空虛感。
等到了自己進入了法律系、法研所的時候,民眾對司法體系的不滿及憤怒已經像是即將爆炸的壓力鍋,「恐龍法官」等近乎人身攻擊的詞彙在輿論市場竄升,本應最受社會敬重的法官、檢察官及律師(好吧,或許律師不能算,因為律師一直都被當成「魔鬼代言人」),死刑廢除的爭議也浮上檯面,有趣的是不信任司法體系的人民並沒有想要取消司法體系藉由死刑殺人的權力,相反地,2014年廢死聯盟委託中研院所做的調查,69%的人對台灣司法判決的公平性沒有信心,超過一半(54%)的人對於死刑的判決不抱信心,卻有77%的受訪者表示雖然知道有死刑誤判的狀況存在,但他們仍然支持死刑。
然而我們卻從沒能真正認識死刑。我在參加律師訓練的時候,藉由參訪臺北看守所的機會一睹刑場的樣貌,半露天的舍房內放了孫逸仙的照片(所謂的國父遺像)、國旗以及幾張桌子,讓指揮執行的檢察官得以代表國家及人民鎮坐現場目睹一切發生,據獄方的說法,現在已經不讓死刑犯站著受刑,改由死刑犯趴在被單上,由法警持槍近距離朝受刑人背後靠近心臟處射擊,避免血液噴的到處都是而讓亡靈怨氣無法散去。
死刑作為刑罰手段,表示這個國家認為殺人是項合理的處罰措施。人犯錯應該要受罰,藉此為自己犯下的罪行付出代價,進而還受難的被害者及其家屬一個公道。因此每當有人犯伏法,大批媒體莫不搶先以獨家快訊將「死訊」昭告天下,激動而難掩興奮的鄉民留言暗示了死刑這項「實現正義的儀式」在台灣不僅仍被視為不可或缺,更貌似是台灣社會制度神聖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處罰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還被害者公道?安撫被害者及家屬?還是彰顯法律無邊威力來恫嚇人民不可犯法?有些人會說,死刑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因為不符合修復式司法的理念,但我們無法假設每個被害人都希望自己與加害者間的關係獲得修復,也有為數不少的人群認為,現在的死刑太過溫和,應該設法讓這些罪人感受到更多的痛楚。但我們應該直接面對更加尖銳的問題:某些人確實惡性重大,徒死恐不足以彌補其罪行,但奪取生命作為處罰的意義,究竟代表著什麼?
而除了滿足若干情緒以及平撫恐懼外,死刑似乎也無法做的更多了。對我來說,奪取生命的死刑,無疑是以人為方式刪除死刑犯的所有可能性,例如畢業的學生正要邁入職場展開新旅程,退休的勞工也能在晚年生活為自己的人生寫下另一篇精彩的篇章,相較於被監禁在舍房內的犯人仍能從事極度有限的事業,死刑則讓人犯的生命畫下句點,這個社會也不再與他有任何羈絆,然而留下的瓜葛卻不會因此不見,被害者的傷痛、還沒被翻轉的社會結構,甚至有一群沈默而長年被遺忘的死刑被害人:死刑犯家屬,這些人、這些事,在槍聲響起後,是否還會有人在意?
對於台灣社會來說,談論死刑或許過於早熟,因為我們都還沒能認識死刑的樣貌,就要思考死刑的意義,因此不論你支持死刑或反對死刑,都建議透過這本書一窺死刑的真實樣貌(即使抱持著偷窺刑場的八卦心態),必定將會讓我們對死刑有更多不同的看法。
第7章 你再看一次 「因為拿破崙‧比茲利在十七歲時犯下的案子,美國政府打算在2001年8月15日殺死他。如果拿破崙‧比茲利住在中國、葉門、吉爾吉斯、肯亞、俄羅斯、印尼、日本、古巴、新加坡、瓜地馬拉、喀麥隆、敘利亞,或是任何其他仍保有死刑的國家,他的命運就不會是如此。然而,他住在美利堅合眾國,正等著被處死。」——國際特赦組織 「當你的丈夫在你的面前被殺死;當你的父親被人從你的生命中奪走時,即使用千言萬語也無法形容這一切——那種驚恐、哀痛、空虛、絕望、混亂和困惑……彷彿生命頓時失去了意義……。發生在我身上的這種犯罪案件,在任何號稱自由文明的社會都是無法被容忍的。」——小約翰‧邁可‧路提格,拿破崙‧比茲利一案被害人,約翰路提格的兒子 拿破崙‧比茲利揮出「一桿進洞」,在行刑前最後一刻,被德州刑事上訴法院(Texas Court of Criminal Appeals)准予暫緩執行。但2002年4月,在他被關進死囚室七年之後,他的暫緩令被撤銷,並且重新排定在下個月執行死刑。在我為《亨茨維爾簡報》採訪他的那幾個月,我見過他很多次。因為他是青少年死刑的代表人物,很多家媒體都想報導他。進入監獄體系工作後,我逐漸退居幕後,開始用不同的角度看待拿破崙。 因為我們有著類似的成長背景,而且年紀相仿,我們相處得十分融洽。他是個有趣的傢伙,時常會開些小玩笑。有一次他問我,我的工作內容是什麼。當我告訴他之後,他說:「你目睹死刑?那真是爛屎了!」我把這句話寫了下來,因為我覺得實在太好笑了。 還有些犯人似乎對自己犯下的罪行真心感到愧疚;大部分的死刑犯不是一開始就打算做這些事。他們其實並非心理病態,因為他們不是某天早上起床後,就決定要殺了某個人。也許他們一開始只打算到某個人家行竊或搶劫某個人,最後卻殺了他。然而,拿破崙的狀況又完全不同。
 好心情好人生:發揮正面心念的強大力量
好心情好人生:發揮正面心念的強大力量 轉化心念福滿人間
轉化心念福滿人間 莎拉的白魔法Ⅱ:善用吸引力法則的正...
莎拉的白魔法Ⅱ:善用吸引力法則的正... 心念自癒力:突破中醫、西醫的心療法
心念自癒力:突破中醫、西醫的心療法 疾病是心念的投射
疾病是心念的投射 感恩日記:每天寫下一件令你感恩的事...
感恩日記:每天寫下一件令你感恩的事... 心念:25堂從情緒引導學習的內在課程
心念:25堂從情緒引導學習的內在課程 轉化心念:淨化人間心樂園(2片CD...
轉化心念:淨化人間心樂園(2片CD...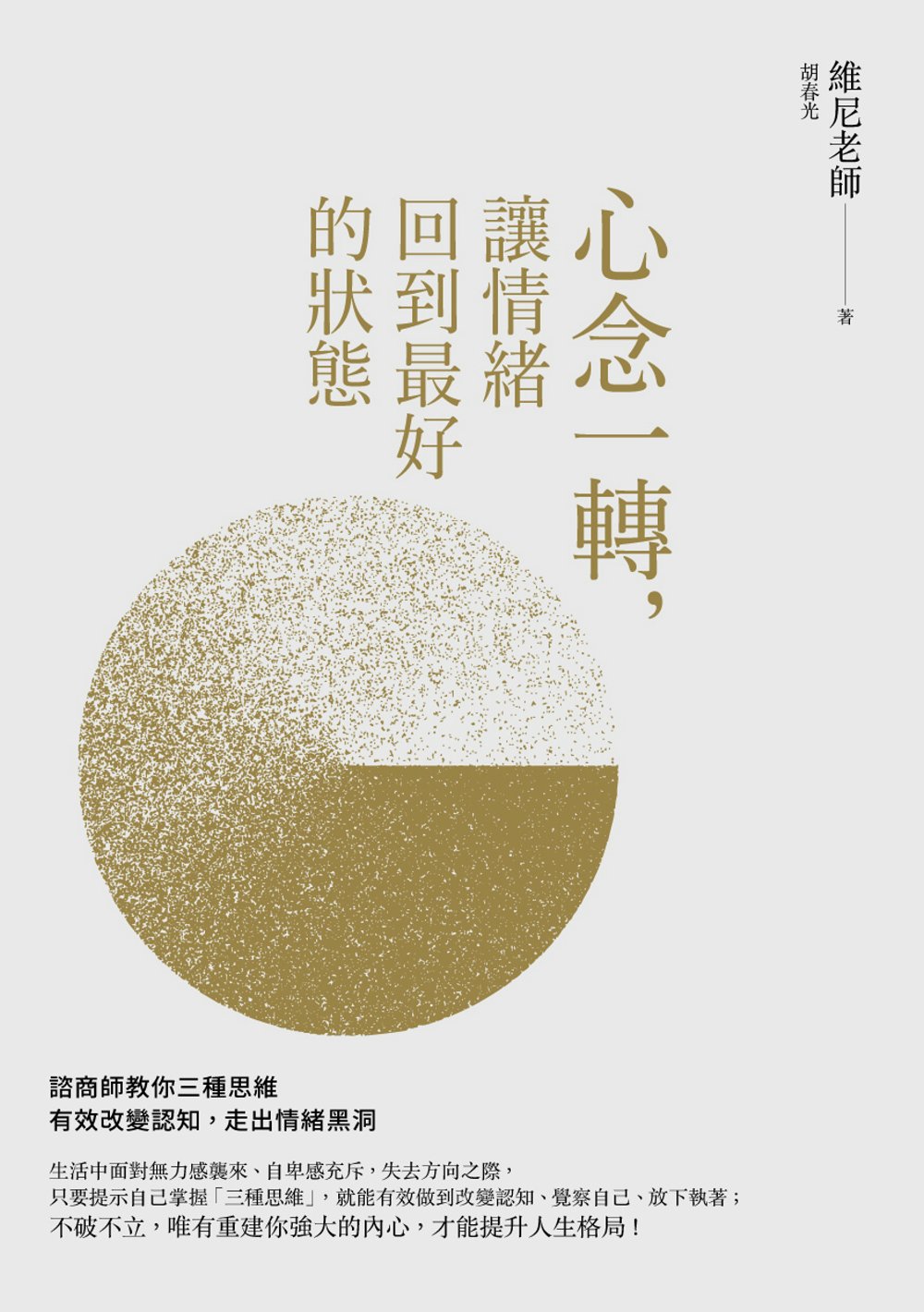 心念一轉,讓情緒回到最好的狀態:諮...
心念一轉,讓情緒回到最好的狀態:諮... 積善:生命的改變,始終源於心念
積善:生命的改變,始終源於心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