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向腦看:我們正在用還在演化中的腦去理解那演化而來的腦 | 維持健康的好方法 - 2024年11月

科學向腦看:我們正在用還在演化中的腦去理解那演化而來的腦
科普書的品質與數量,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科普寫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要寫得好,除了要具有豐厚的專業知識之外,更要有「好為人師」的熱情,也就是說,永遠要不停的問:如何才能讓讀者了解手上這些新近的科學知識?如何激起他們的好奇心?如何讓他們看到核心問題的本質?如何讓問題的困境形成懸疑?如何展現科學解題歷程中的美好推論?如何讓讀者看到好的科學家就是會在眾多的可能性中選對了方向?如何讓學生體會在各方研究者一齊搶灘的環境中,終能捷足先登的快感?還有,要如何鋪陳人類文明進展的史觀,使讀者感受到科學新知的喜悅之情?當然,寫作的文采,更是使科普著作能感動讀者的最基本原素。
曾志朗本著如此的信念,為了台灣的文明盡心盡力,以從不衰減的熱情,帶領讀者越過知識的高牆,領略科學之美。
〈推薦序〉
做為科學人的堅持 王力行
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聯合報》《中國時報》兩大報的頭條都是〈曾志朗公開倒扁〉〈中研院副院長曾志朗:捐百元,精神支持倒扁〉。
這則新聞的震撼力,一方面是因為曾志朗身居全國最高學術機構的第二高位;另一方面曾副院長是一位隨和有人緣,又對社會充滿熱情的科學人。
他在訪問中說:「社會上要的是誠實及純樸表率,」否則如何教孩子?
他又說,容忍不同意見、保護異議者是民主的真諦;每個人都有表達不同意見的權利,社會攻擊不同意見的行為太過分,台灣就會走回頭路。
讀過他的著作,聽過他的演講,熟識他的人應該不會訝異,這就是曾志朗知識分子的誠正性格,以及科學人所堅持的多元價值。
這位致力於「認知神經科學」研究的中研院院士,終究是位教育家。他對在台灣普及科學知識,始終懷抱理想,堅信「科學知識一定要系統化,才能驗證,才能發展機制,提升理論水平」。
因此,每個月在《科學人》雜誌上,總能讀到他以豐美的文采、國際的閱歷和深厚的專業知識,寫出一篇篇引人入勝的文章。
他更是位科學家,在他身上可以見到科學家的特徵:強烈的求知慾和對知識分享的熱情。
當別人對「心理學也要做實驗」提出問號時,他最想做的一件事是寫一本科普心理學,把百年心理學如何「從沙發上的冥思走進實驗室」的過程,做個深入淺出的說明。讓大家瞭解「科學的心理學」是需要實驗研究和數據證明的。
這本《科學向腦看》是曾志朗院士把三年來在《科學人》雜誌上膾炙人口的專欄文字集結成冊。寫書和教書的曾志朗,在文字中充分顯露他做為科學人的求真,和教育家的求善與求美的特質。
讀他的文章是一種享受,他擅於輕鬆愉快地導引讀者進入知識的殿堂。
在書中,他總會先帶出引人嚮往的場景,如柏林郊外的花園旅社、地中海沿的亞歷山大港、紐約中央公園的雪花;或者出現有趣的人物,如大科學家、當年當兵的排副、患失讀症的影視名人,甚至會對唱的公鳥和母鳥。
故事說到關鍵處,他會把重點轉進「認知」知識的領域——記憶、文化認知、思維、原創力、老化……,展開冷靜理性的探討並提出他的讚嘆、懷疑或建議。
這樣一位科學知識教育者,從人類基因的發展、腦的發展,來分析人的語言、文字、思考、智慧,最終目的無非在推動人類文明、社會進步、人格品質提升。
也因此對抗拒社會的不公、不義、不法特別堅持。正如他在另一本著作《見人見智》中寫道:「我們因為常常聽到大家說南部的紅綠燈是參考用的,而笑成一團,其實是在容忍不法;當我們聽到『數位落差』而不以為意時,其實是在容忍不公;當我們把慰安婦悲哀歸因於戰爭的必要之惡時,是在容忍不義。」
讀了這本《科學向腦看》,不僅瞭解科學通識對人們知識的重要,更能理解科學人的堅持對人品的重要了。
【推薦者簡介】
王力行,政大新聞系畢業,曾任職於《綜合月刊》、《婦女雜誌》、《時報雜誌》。《天下》雜誌創辦,擔任副總編輯,後任《遠見》雜誌發行人兼總編輯、天下遠見出版公司發行人,現為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發行人兼事業群總編輯。著有《請問,總統先生》、《無愧──郝柏村的政治之旅》、《寧靜中的風雨──蔣孝勇的真實聲音》、《鬧中取靜》、《字裡行間》(均由天下文化出版)等書。
自序
永遠的科學人
雲出草山入南港
用心動腦盡傾囊
清風巧撥世間霧
解迷且待科學人
離開美國的教職回到台灣,一轉眼就過了十七個年頭了。
這中間我除了教書、研究之外,也一直在學術行政的崗位上努力。剛回台灣的那幾年,在嘉義民雄的甘蔗園裡,看著中正大學宏偉的黌宇校舍,由土地上一尺、一尺的「長高」,然後教授、學生們都來了,實驗室的設備一件又一件補齊,圖書館的書和資訊的平臺也逐漸充實,幾年之間,台灣南部有了一間教研實力相當雄厚的全新大學。在那些日子裡,我也為聯合報繽紛版寫「科學向前看」的科普小品,後來集結成冊,書名是《用心動腦話科學》!
為了開拓認知與神經科學的研究領域,我加入了台灣第一部功能性磁共振造影(fMRI)設備之建構,開始以榮陽團隊的名義發表腦與認知的研究論文,以新的腦顯影技術展示閱讀中文的腦神經活動;我們也希望能由基因到神經系統到行為表現到認知歷程的整體運作中,去理解人腦演化的規律。這段日子,我一方面繼續寫科普小品,一方面也對教育改革的方向提出一些建言,誰知道會因為後者而忽然被延攬入閣,成為政權變革後的第一任教育部長。
負責全國教育行政工作,就在九二一地震垮了近百間災區學校之後不久。我和同仁們全力投入校園重建的工作,提倡新校園運動,規劃智慧型校園的建築計畫,爭取最有利標的推動,直至這些帶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新校舍一處一處完成。新校園運動倡導的學校永續發展的概念,和我任內所提出的「推動閱讀」、「生命教育」、「資訊教育平臺」、「創造力教育」等四個教育政策主軸,目的都是在為台灣的學生建立科技文化的環境,尤其是希望學生在新知識的吸收、理解、轉輸與創作上,能養成自發主動的態度。因此,在高等教育上,我也啟動了大學分類的實質方案,並撥專款推動卓越教學,以提昇通識教育的品質。這些日子,人在行政單位,但念茲在茲的還是科學研究,心中也仍然記掛著科普教育,自己卻因為事務繁忙沒有多餘的時間寫稿了。可是,一有機會,我會為好的科普書寫推薦文,也會在各種場合做科普相關的演說。然後,一直到二○○二年二月《科學人》雜誌在台灣完成出版的事宜,我才能全力去寫我想要提出的一些觀點。
引進一百五十年歷史的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是遠流王榮文和我長久以來的心願,因為種種原因,我們能在二○○二年為台灣的科普工作圓夢。而就在這個時候,我離開政府的職位,回到學術研究單位,當了中研院新增的副院長。科學教育是我的工作重點之一,因此就順其自然的成為台灣《科學人》雜誌的名譽社長,所負的任務是為每一期的《科學人》寫一篇「科學人觀點」。幾年下來,這個專欄也疊積了相當多的文章,和其他科普小品文章在二○○四年集結成冊,書名是《人人都是科學人》,其中最重要的喊話是「賽先生」與「德先生」是同卵雙生子,兩者成長健全,才是現代科技社會文化(STS)的基石。
轉眼,《科學人》已脫離嬰兒期了,我也在二○○六年年底接任了一個沒有校園、沒有預算、沒有人事,當然也沒有薪水的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校長。但當我和清華、交通、陽明、中央四個台灣頂尖研究型大學的校長們聚在借用的會議室裡,大家的心裡都非常充實。這是個meta的組合,用的是抽象的智慧,去增強四校各自的特色,以完成四校無遠弗屆的共同成長。空並不是空,同心合意,則無中生有,本是創意人的本事。因為這十多年,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所推動的每一項工作,想傳達的是,台灣不但要有大學,更要有大學文化;不但要有科學家,更要有科學文化!
編輯告訴我,又到了集結出書的時候。這一本書裡的文章,有四分之三來自「科學人觀點」,另外的四分之一,表面上看是一些應景、應情之作,其實它們都是我心目中和推動科學文化相關的作品。
為了定書名,我也想了很久,後來決定用《科學向腦看》,是一方面反映我自己這十幾年來為台灣所搭建的認知與神經科學的研究平臺,另一方面也是近兩三年「科學人觀點」裡的一個綜合觀測。科學家由四方八面而來,帶著他們各自的專業,把研究的眼光專注到那個讓自己能夠建構出這精深專業知識的「腦袋」!
是的,科學家正在用尚在演化成多元思維的腦,去瞭解腦的演化歷程!科學確實是要向腦看了,下一個研究主題當然就是「人的心靈及其複雜性」(Human Mind and Complexity)!
林布蘭的眼睛其實看畫確是可以看出很多道理的! 自從把《達文西密碼》狠狠的快速閱讀兩次(一次看原文本,一次看中譯本)之後,我忽然對西洋的宗教及人物畫產生神秘的好奇心,走進畫廊看到一幅幅的畫,我不由自主的就一一仔細研讀,總以為在畫中會有隱藏的訊息,待我這有心人去解讀。上星期去一位篤信基督教的朋友家,客廳裡掛了一幅米開朗基羅的「創世紀」名畫的複製品,我就如顛似癡的研究起來,希望在裡面找到一些啟示的秘箴。朋友待我全神貫注的掃描一番,也讓我有充份的時間屏息尋秘,然後說:「有何發現?」 我胸已有定見,就拉著朋友到畫前,品評一番:「創世紀這張畫真是有意思極了!一般通俗的解釋是,上帝坐在飄浮的雲朵中,在幾位小天使的歡樂護擁下,伸出右手的手指,把『生命』傳到一旁的亞當的左手手指上,這是創世紀中人類生命由來的故事。依我的看法,這樣的說法是錯的。米開朗基羅真是個天才的先知!他畫的並不是上帝把生命傳給亞當,而是把『智慧』傳給亞當,畫中充滿了各種線索,不斷在暗示這一個訊息。例如,畫中的亞當栩栩如生,哪需再加持生命;你再仔細看,上帝的手指和亞當的手指並沒有直接接觸,而是保留一小間隔,這個暗示太重要了,現代神經科學家在最近幾十年才了解,神經元和神經元之間的傳導不是如一條電線和另一條電線必須接觸才能導電,而是經由在神經突觸和突觸之間的離子的平衡狀態的破壞,而導致另一條神經的活化,這個電化作用是一切學習的基礎,所以米氏的畫所揭示的是,上帝把學習的機能傳給了亞當,而且最重要的是,這個機制來自人類的左腦,是理性的本源所在地!」 我看朋友一臉不信的樣子,就指著畫中承載上帝的雲朵,向他仔細解說:「你看那朵雲的樣子像什麼?是不是像人類大腦解剖圖中的左腦半球的形狀,連分開左前腦和左後腦的迴溝都那麼清楚可見。米開朗基羅若不是先知,怎可能在五百多年前就了解了左腦擁有人類邏輯推理的功能,所以他要上帝把真正的智慧傳給亞當,做為給人類的禮物!」 我可以從一張畫中看出這麼多啟示,朋友雖然不服氣,卻不得不佩服我穿鑿附會的本事。但他仍試圖「教育」我一番,說:「你講得煞有介事,但都是事後解釋,雖然有許多巧合,但並沒有其他獨立的數據來加以佐證。科學是講究證據與證據之間系統性的因果關係,不是像這樣看到什麼像什麼,就一定是什麼的論述方式!」 聽到朋友這一席科學感言,我就放心的把適才的偽裝全部卸下,恢復了科學人的本體之後,再次發言:「我完全同意你的說理,可是時下多的是這種神話連篇的科幻故事,稍一不慎,就以為有了科學的新發現了。客觀的檢驗,才是一切科學證據的基礎。其實看畫確實可以看出很多道理的!哈佛醫學院的兩位視神經科學家對林布蘭的最新研究,就是最佳見證。」 我在他的書架上,找到了一本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的畫冊,翻開林布蘭從年輕到年老的十幾幅自畫像,我拿尺仔細測量每一幅畫中兩隻眼睛的瞳孔位置,看看水晶體旁的眼白部份是否對稱,這樣就可以算出每一隻眼珠的凝視點。仔細比對之後,很明顯的事實出現了,林布蘭的兩隻眼睛凝視點都不同,這表示他可能是看不到立體的形狀的。這麼偉大的畫家竟然沒有立體的知覺,這不是很奇怪嗎?但是,記得我們上繪畫課時,老師總是要求我們把一隻眼睛閉起來,只用一隻眼睛去感知物件的顏色。所以,林布蘭的「立體盲」應該不會造成太大的負面影響,反而可能因為他對顏色的感知比別人都強烈,造就了一個劃時代的畫家! 朋友頗不服氣(科學人要的就是挑戰精神)──嫌畫冊的圖像太小,眼睛的測量過於粗略,他馬上上網去尋找這個荷蘭畫家的數位化作品。在螢幕上,加以放大,讓眼睛的黑白更為分明。他埋頭苦幹了幾小時後,抬頭對我說:「你對了,林布蘭確實是個『脫窗』!」 所以,只有讓好品質的證據呈現,才是好科學!
 積善:生命的改變,始終源於心念
積善:生命的改變,始終源於心念 回天的五個條件-心念
回天的五個條件-心念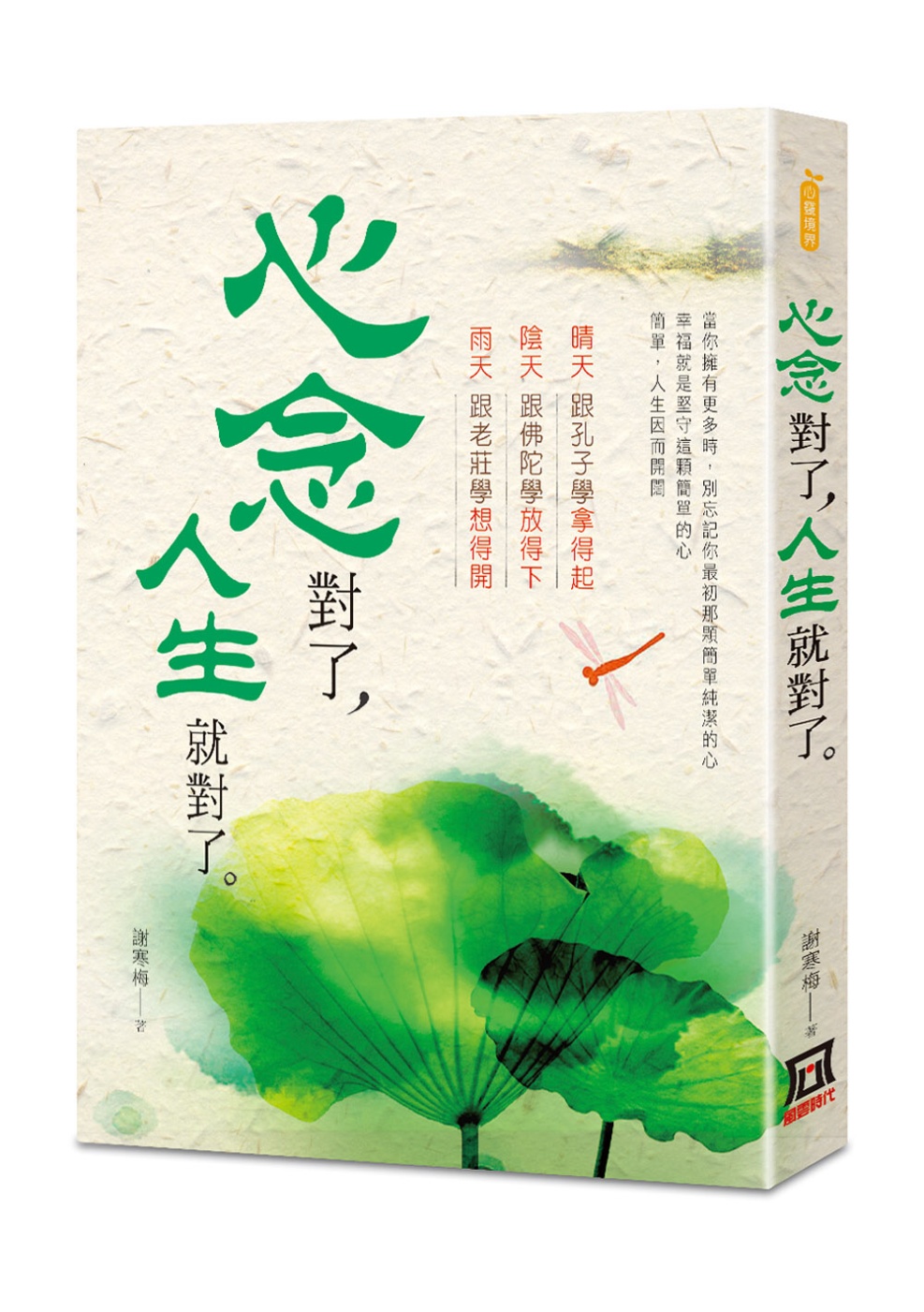 心念對了,人生就對了
心念對了,人生就對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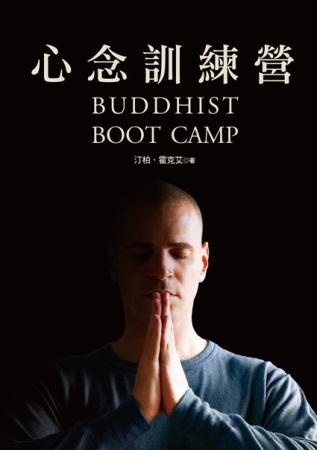 心念訓練營
心念訓練營 世界最偉大的心念力
世界最偉大的心念力 三十六萬遍感恩的奇蹟:所有生命都是...
三十六萬遍感恩的奇蹟:所有生命都是... 轉化心念:淨化人間心樂園(2片CD...
轉化心念:淨化人間心樂園(2片CD... 簡單豐足:減法養生的52個關鍵字
簡單豐足:減法養生的52個關鍵字 心念自癒力:突破中醫、西醫的心療法
心念自癒力:突破中醫、西醫的心療法 好心情好人生:發揮正面心念的強大力量
好心情好人生:發揮正面心念的強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