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的合金 | 維持健康的好方法 - 2024年7月

月光的合金
收錄了格麗克的四本詩集,《野鳶尾》(普利策詩歌獎)、《草場》、《新生》(《紐約客》詩歌圖書獎)、《七個時期》(普利策詩歌獎短名單),均為成熟期的重要作品。露易絲•格麗克(Louise Glück,1943— ),美國桂冠詩人,生於一個匈牙利裔猶太人家庭,1968年出版處女詩集《頭生子》,至今着有十二本詩集和一本詩隨筆集,遍獲各種詩歌獎項,包括普利策獎、國家圖書獎、全國書評界獎、美國詩人學院華萊士•斯蒂文斯獎、波林根獎等。格麗克的詩長於對心理隱微之處的把握,早期作品具有很強的自傳性,后來的作品則通過人神對質,以及對神話人物的心理分析,導向人的存在根本問題,愛、死亡、生命、毀滅。自《阿勒山》開始,她的每部詩集都是精巧的織體,可作為一首長詩或一部組詩。從《阿勒山》和《野鳶尾》開始,格麗克成了「必讀的詩人」。
代譯序:露易絲 • 格麗克的疼痛之詩野鳶尾野鳶尾晨禱晨禱延齡草野芝麻雪花蓮晴朗的早晨春雪冬天結束晨禱晨禱藍鍾花遠去的風花園山楂樹月光中的愛四月紫羅蘭女巫草花蔥晨禱晨禱歌曠野的花紅罌粟三葉草晨禱天堂與大地門仲夏晚禱晚禱晚禱雛菊夏天結束晚禱晚禱晚禱最初的黑暗豐收白玫瑰牽牛花普雷斯克艾爾遠去的光晚禱晚禱:基督再臨晚禱晚禱日落催眠曲銀百合九月的曦光金百合白百合草場珀涅羅珀之歌迦拿寧靜夜禮儀國王的寓言無月之夜別離伊薩卡忒勒馬科斯的超然人質的寓言下雨的早晨藤架的寓言忒勒馬科斯的罪周年草場 1忒勒馬科斯的善良禽獸的寓言午夜塞壬草場 2船塢鴿子的寓言忒勒馬科斯左右為難草場 3岩石喀耳刻的威力忒勒馬科斯的奇想飛翔的寓言奧德修斯的決定返鄉蝴蝶喀耳刻的痛苦喀耳刻的悲傷珀涅羅珀的固執忒勒馬科斯的告白空虛忒勒馬科斯的重負天鵝的寓言紫色泳衣忠誠的寓言重聚夢奧蒂斯許願禮物的寓言心的欲望新生新生晨曲迦太基女王敞開的墳墓習慣法燃燒的心羅馬研究新生活奶酪對死亡的恐懼魯特琴之歌俄耳甫斯降臨山谷外衣公寓永生之愛俗世之愛歐律狄刻卡斯提爾無常的世界飛馬世俗的恐懼金枝12夜禱廢墟鳥巢埃爾斯沃思大道地獄發作偵探小說哀悼新生七個時期七個時期月光感官的世界母親與孩子寓言夏至日星13青春尊貴的畫像重聚鐳生日古代文本來自一份雜志島目的地陽台紫葉山毛櫸研究妹妹八月海濱之夏夏雨文明十年空杯榲桲樹旅行者植物園欲望之夢恩典寓言幸福的繆斯成熟的桃子未上漆的門有絲分裂愛洛斯計策時間自傳聖女貞德晨曲紗窗門廊夏夜寓言
最初讀到格麗克,是震驚!僅僅兩行,已經讓我震驚——震驚於她的疼痛:我要告訴你件事情:每天人都在死亡。而這只是個開頭。露易絲•格麗克的詩像錐子扎人。扎在心上。她的詩作大多是關於死、生、愛、性,而死亡居於核心。經常像是宣言或論斷,不容置疑。在第一本詩集中,她即宣告:「出生,而非死亡,才是難以承受的損失。」(《棉口蛇之國》)從第一本詩集開始,死亡反復出現,到1990年第五本詩集《阿勒山》,則幾乎是一本死亡之書。第六本詩集《野鳶尾》轉向抽象和存在意義上的有死性問題。此后的詩集,死亡相對減少,但仍然不絕如縷。與死亡相伴的,是對死亡的恐懼。當人們戰勝死亡、遠離了死亡的現實威脅,就真能擺脫對死亡的恐懼、獲得安全和幸福嗎?格麗克的詩歌給了否定的回答。在《對死亡的恐懼》(詩集《新生》)一詩里,詩人寫幼年時的一個噩夢,「當那個夢結束/恐懼依舊。」在《愛之詩》里,媽媽雖然一次次結婚,但一直含辛茹苦地把兒子帶在身邊,給兒子「織出各種色調的紅圍巾」,希望兒子有一個溫暖、幸福的童年。但結果呢?詩中不露面的「我」對那個已經長大的兒子說:「並不奇怪你是現在這個樣子,/害怕血,你的女人們/像一面又一面磚牆。」或許只有深諳心理分析的詩人才會寫出這樣的詩作。《黑暗中的格萊特》是又一個例子。在這首類似格萊特獨白的詩作中,格麗克對格林童話《漢賽爾與格萊特》皆大歡喜的結局深表懷疑:雖然他們過上了渴望的生活,但所有的威脅仍不絕如縷,可憐的格萊特始終無法擺脫被拋棄的感覺和精神上的恐懼——心理創傷。甚至她的哥哥也無法理解她、安慰她。而這則童話中一次次對飢餓的指涉,也讓我們想到格麗克青春時期為之深受折磨的厭食症。終於,在《花園》這個組詩里,她給出了「對出生的恐懼」、「對愛的恐懼」、「對埋葬的恐懼」,儼然是一而三、三而一。由此而言,逃避出生、逃避愛情也就變得自然而然了。如《聖母憐子像》一詩中,格麗克對這一傳統題材進行了改寫,猜測基督:「他想待在/她的身體里,遠離/這個世界/和它的哭聲,它的/喧囂。」又如《寫給媽媽》:「當我們一起/在一個身體里,還好些。」格麗克詩中少有幸福的愛情,更多時候是對愛與性的猶疑、排斥,如《夏天》:「但我們還是有些迷失,你不覺得嗎?」她在《伊薩卡》中寫道:「心愛的人/不需要活着。心愛的人/活在頭腦里。」而關於愛情的早期宣言之作《美術館》寫愛的顯現,帶來的卻是愛的泯滅:「她再不可能純潔地觸摸他的胳膊。/他們必須放棄這些……」格麗克在一次訪談中談到了這首詩:「強烈的身體需要否定了他們全部的歷史,使他們變成了普通人,使他們淪入窠臼……在我看來,這首詩寫的是他們面對那種強迫性需要而無能為力,那種需要嘲弄了他們整個的過去。」這首詩強調的是「我們如何被奴役」。格麗克詩歌中遠非個案,顯示格麗克似乎是天賦異稟。一直到《阿基利斯的勝利》一詩,格麗克給出了愛與死的關系式。這首詩寫阿基利斯陷於悲痛之中,而神祇們明白:「他已經是個死人,犧牲/因為會愛的那部分,/會死的那部分」,換句話說,有愛才有死。在《對死亡的恐懼》(詩集《新生》)中再次將愛與死進行等換:「每個恐懼愛的人都恐懼死亡。」這其實是格麗克關於愛與死的表達式:「愛=>死」,它與《聖經•創世記》所表達的「獲得知識=>遭遇有死性」、扎米亞金所說的「π=f(c),即愛情是死亡的函數」有異曲同工之妙。按《哥倫比亞美國詩歌史》里的說法,「從《下降的形象》(1980)組詩開始,格麗克開始將自傳性材料寫入她凄涼的口語抒情詩里」。這里所謂的自傳性材料,大多是她經歷的家庭生活,如童年生活,姐妹關系,與父母的關系,親戚關系,失去親人的悲痛。她曾在《自傳》一詩(《七個時期》)中寫道:「我有一套愛的哲學,宗教的/哲學,都是基於/早年在家里的經驗。」后期詩歌中則有所擴展,包括青春、性愛、婚戀、友誼……逐漸變得抽象,作為碎片,作為元素,作為體驗,在詩作中存在。這一特點在詩集《新生》《七個時期》《阿弗爾諾》中非常明顯。更多時候,自傳性內容與她的生、死、愛、性主題結合在一起,詩集《阿勒山》堪稱典型。同時,抒情性也明顯增強,有些詩作趨於純粹、開闊,甚至有些玄學的意味。羅伯特•海斯(RobertHass)曾稱譽格麗克是「當今寫作者中,最純粹、最有成就的抒情詩人之一」,可謂名至實歸。因此,格麗克詩歌的一個重要特點就在於她將個人體驗轉化為詩歌藝術,換句話說,她的詩歌極具私人性,卻又備受公眾喜愛。但另一方面,這種私人性絕非傳記,這也是格麗克反復強調的。她曾說:「把我的詩作當成自傳來讀,我為此受到無盡的煩擾。我利用我的生活給予我的素材,但讓我感興趣的並不是它們發生在我身上,讓我感興趣的,是它們似乎是……范式。」實際上,她也一直有意地抹去詩歌作品以外的東西,抹去現實生活中的作者對讀者閱讀作品時可能的影響,而且愈來愈決絕。比如,除了1995年早期四本詩集合訂出版時她寫過一頁簡短的「作者說明」外,她的詩集都是只有詩作,沒有前言、后記之類的文字——就是這個簡短的「作者說明」,在我們准備中文版過程中,她也特意提出不要收入。譯者曾希望她為中文讀者寫幾句話,也被謝絕了;她說她對這本書的貢獻,就是她的詩作。此外,讓她的照片、簽名出現在這本詩選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格麗克出生於一個敬慕智力成就的家庭。她在隨筆《詩人之教育》一文中講到家庭情況及早年經歷。她的祖父是匈牙利猶太人,移民到美國后開雜貨鋪謀生,但幾個女兒都讀了大學;的兒子,也就是格麗克的父親,拒絕上學,想當作家。但后來放棄了寫作的夢想,投身商業,相當成功。在她的記憶里,父親輕松、機智,最拿手的是貞德的故事,「但最后的火刑部分省略了」。少女貞德的英雄形象顯然激起了一個女孩的偉大夢想,貞德不幸犧牲的經歷也在她幼小心靈里投下了死亡的陰影。她早年有一首《貞德》(《沼澤地上的房屋》);后來還有一首《聖女貞德》(《七個時期》),其中寫道:「我相信我將要死去。我將要死去/在十歲,死於兒麻。我看見了我的死亡:/這是一個幻象,一個頓悟——/這是貞德經歷過的,為了挽救法蘭西。」格麗克在《詩人之教育》中回憶說:「我們姐妹被撫養長大,如果不是為了拯救法國,就是為了重新組織、實現和渴望取得令人榮耀的成就。」格麗克的母親尤其尊重創造性天賦,對兩個女兒悉心教育,對她們的每一種天賦都加以鼓勵,及時贊揚她的寫作。格麗克很早就展露了詩歌天賦,並且對詩歌創作野心勃勃。在《詩人之教育》中抄錄了一首詩,「大概是五六歲的時候寫的」。十幾歲的時候,她比較了自己喜歡的畫畫和寫作,最終放棄了畫畫,而選擇了文學創作,並且野心勃勃。她說:「從十多歲開始,我就希望成為一個詩人。」格麗克提到她還不到三歲,就已經熟悉希臘神話。縱觀格麗克的十一本詩集,她一次次回到希臘神話,隱身於這些神話人物的面具后面,唱着冷冷的歌。「到青春期中段,我發展出一種症狀,完美地親合於我靈魂的需求。」格麗克多年后她回憶起她的厭食症。她一開始自認為是一種自己能完美地控制、結束的行動,但結果卻成了一種自我摧殘。十六歲的時候,她認識到自己正走向死亡,於是在高中臨近畢業時開始看心理分析師,幾個月后離開了學校。以后七年里,心理分析就成了她花時間、花心思做的事情。格麗克說:「心理分析教會我思考。教會我用我的思想傾向去反對我的想法中清晰表達出來的部分,教我使用懷疑去檢查我自己的話,發現躲避和刪除。它給我一項智力任務,能夠將癱瘓——這是自我懷疑的極端形式——轉化為洞察力。」而這種能力,在格麗克看來,於詩歌創作大有益處:「我相信,我同樣是在學習怎樣寫詩:不是要在寫作中有一個自我被投射到意象中去,不是簡單地允許意象的生產——不受心靈妨礙的生產,而是要用心靈探索這些意象的共鳴,將淺層的東西與深層分隔開來,選擇深層的東西。」(《詩人之教育》)對格麗克來說,心理分析同時促進了她的詩歌寫作,二者一起,幫助她最終戰勝了心理障礙。十八歲,格麗克在哥倫比亞大學利奧尼•亞當斯(LeonieAdams)的詩歌班注冊學習,后來又跟隨老一輩詩人斯坦利庫尼茲(StanleyKunitz)學習。庫尼茲與羅伯特•潘•沃倫同年出生,曾任2000—2001年美國桂冠詩人。按格麗克的說法,「跟隨斯坦利•庫尼茲學習的許多年」對她產生了長久的影響;她的處女詩集《頭生子》即題獻給庫尼茲。1968年,《頭生子》出版,有評論認為此時的格麗克「是羅伯特•洛威爾和希爾維亞•普拉斯的一個充滿焦慮的模仿者」。但我看到更明顯的是T.S.艾略特和葉芝的影子。如開卷第一首《芝加哥列車》寫一次死氣沉沉的旅程,不免過於濃彩重墨了。第二首《雞蛋》(III)開篇寫道:「總是在夜里,我感覺到大海/刺痛我的生命」,讓我們猜測是對葉芝《茵納斯弗利島》的摹仿,或者說反寫:作為理想生活的海「刺痛」了她的生活。她后來談到《頭生子》的不成熟和意氣過重,頗有悔其少作的意味,說她此后花了六年時間寫了第二本詩集:「從那時起,我才願意簽下自己的名字。」格麗克雖然出生於猶太家庭,但認同的是英語傳統。她閱讀的是莎士比亞、布萊克、葉芝、濟慈、艾略特……以葉芝的影響為例,除了上面提到的《雞蛋》(III)之外,第二本詩集有一首《學童》(本書中譯為《上學的孩子們》),讓人想到葉芝的名詩《在學童中間》;第三本詩集中那首《聖母憐子像》中寫道:「遠離/這個世界/和它的哭聲,它的/喧囂」,而葉芝那首《偷走的孩子》則反復回盪着「這個世界哭聲太多了,你不懂」。相同的是對這個世界的拒絕,不同的是葉芝詩中的孩子隨精靈走向荒野和河流,走向仙境,而在格麗克詩中,「他想待在/她的身體里」,不想出生——正好呼應了她的那個名句:「出生,而非死亡,才是難以承受的損失。」希臘羅馬神話、《聖經》、歷史故事等構成了格麗克詩歌創作的一個基本面。如作為標題的「阿勒山」、「花蔥」(雅各布的梯子)、「亞比煞」、「哀歌」等均出自《聖經》。《聖母憐子像》、《一則寓言》(大衛王)、《冬日早晨》(耶穌基督)、《哀歌》、《一則故事》等詩作取材於《聖經》。在《傳奇》一詩中,詩人以在埃及的約瑟來比喻她移民到美國的祖父。最重要的是,聖經題材還成就了她最為奇特、傳閱最廣的詩集《野鳶尾》(1992)。這部詩集可以看作是以《聖經•創世記》為基礎的組詩,主要是一個園丁與神的對話(請求、質疑、答復、指令),關注的是挫折、幻滅、希望、責任。在此我們應該有個基本的理解:格麗克是一位現代詩人,她借用《聖經》里的相關素材,而非演繹、傳達《聖經》。實際上,當她的《野鳶尾》出版后,格麗克曾收到宗教界人士的信件,請她少寫關於神的文字。她在詩歌創作中對希臘神話的偏愛和借重,也與此類似。「讀詩的藝術的初階是掌握具體詩篇中從簡單到極復雜的用典。」了解相關的西方文化背景和典故,構成了閱讀格麗克詩歌的一個門檻。如詩集《新生》中《燃燒的心》一詩,開頭引用但丁《神曲•地獄篇》第五章弗蘭齊斯嘉的話,如果熟悉這個背景,那麼整個問答就非常有意思了。接下來的一首《羅馬研究》,如果不熟悉相應的典故,讀起來也是莫名其妙。希臘羅馬神話對格麗克詩歌的重要性無以復加,這在當代詩歌中獨樹一幟,如早期四本詩集中的阿波羅和達佛涅(《神話片斷》)、西西弗斯(《高山》)等。而具有重要意義的,則集中於詩集《阿基利斯的勝利》《草場》《新生》《阿弗爾諾》。如《草場》集中於如奧德修斯、珀涅羅珀、喀爾刻、塞壬等希臘神話中的孤男怨女,寫男人的負心、不想回家,寫女人的怨恨、百無聊賴……這些詩作經常加入現代社會元素,或是將人物變形為現代社會的普通男女,如塞壬「原來我是個女招待」,從而將神話世界與現代社會融合在一起。《新生》的神話部分主要寫埃涅阿斯與狄多、俄耳甫斯與歐律狄克兩對戀人的愛與死,《阿弗爾諾》則圍繞冥后珀爾塞福涅的神話展開。寫到這里,建議讀者有機會溫習下《伊利亞特》《奧德賽》《埃涅阿斯紀》《神曲》,以及《希臘羅馬神話》和《聖經》。當然不用說這些著作本身就引人入勝,拿起來就舍不得放下,這里只說熟悉了相關細節,讀格麗克的詩作會更加興味盎然,甚至有意想不到的發現。比如我發現海子的《十四行:王冠》前兩節是「改寫」自阿波羅對達佛涅的傾訴(允諾),而有些論者的解讀未免不着邊際。當然,於我而言,更多的是考慮翻譯的准確性。如那首《阿基利斯的勝利》,周瓚兄譯為《阿喀琉斯的凱旋》,中文維基百科的「阿喀琉斯」條目引用弗朗茨•馬什描繪阿基利斯殺死赫克托耳后用戰車拖着他的屍體(對應《伊利亞特》第22卷)的畫作,也譯作《阿喀琉斯的凱旋》。但恐怕,「凱旋」一詞說不上恰當,畢竟,阿基利斯是「凱」而不「旋」的,他的勝利就是他的死亡。從《阿勒山》開始,格麗克開始把每一本詩集作為一個整體、一首大組詩(book-lengthsequence)來看待。這個問題對格麗克來說,是一本詩集的生死大事。她曾談到詩集《草場》,她最初寫完了覺得應該寫的詩作后,一直覺得缺了什麼:「不是說你的二十首詩成了十首詩,而是一首都沒有!」后來經一位朋友提醒,才發現缺少了忒勒馬科斯。格麗克說:「我喜歡忒勒馬科斯。我愛這個小男孩。他救活了我的書。」[1]一本詩集怎樣組織、包括哪些詩作、每首詩的位置……格麗克都精心織就。再以《阿弗爾諾》為例,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書評中說:「詩集中的18首詩豐富而和諧:以相互關聯的復雜形象、一再出現的角色、重疊的主題,形成了一個統一的集合,其中每一部分都不失於為整體而言說。」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細加琢磨,並擴展到另外幾本詩集。如此,或能得窺格麗克創作的一大奧秘。
 土耳其是一種癮:順著讀是土耳其版的...
土耳其是一種癮:順著讀是土耳其版的... 奈米金屬微粒暴露作業人員健康危害流...
奈米金屬微粒暴露作業人員健康危害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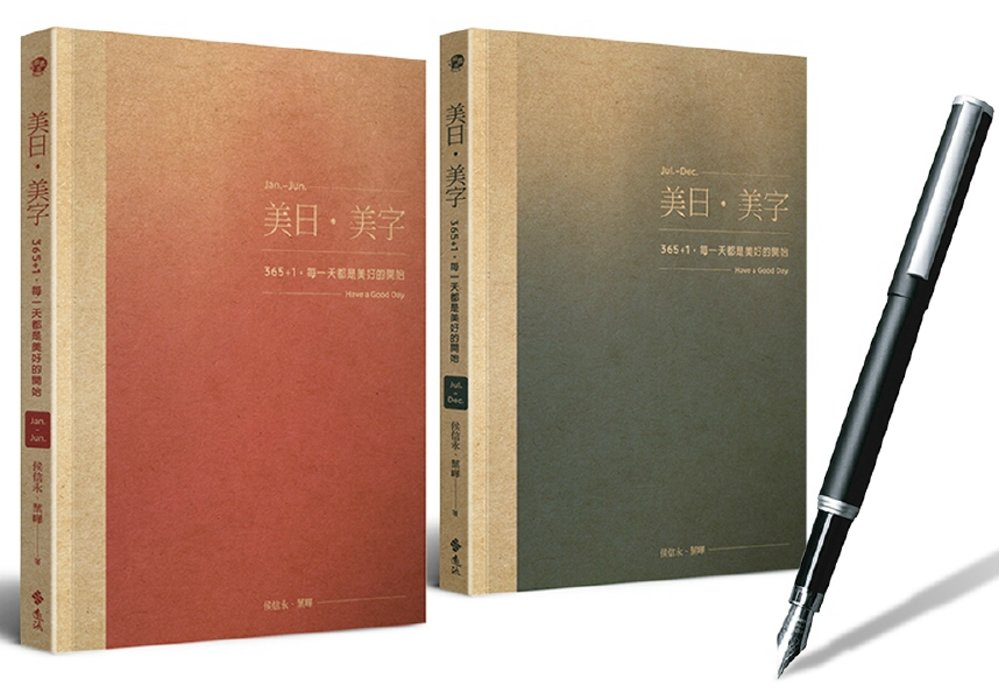 《美日‧美字》寫字+日誌雙書超值套...
《美日‧美字》寫字+日誌雙書超值套... 從起針開始,一次學會手縫皮革基本功
從起針開始,一次學會手縫皮革基本功 高血壓
高血壓 汽車修理業噴漆作業勞工重金屬暴露調...
汽車修理業噴漆作業勞工重金屬暴露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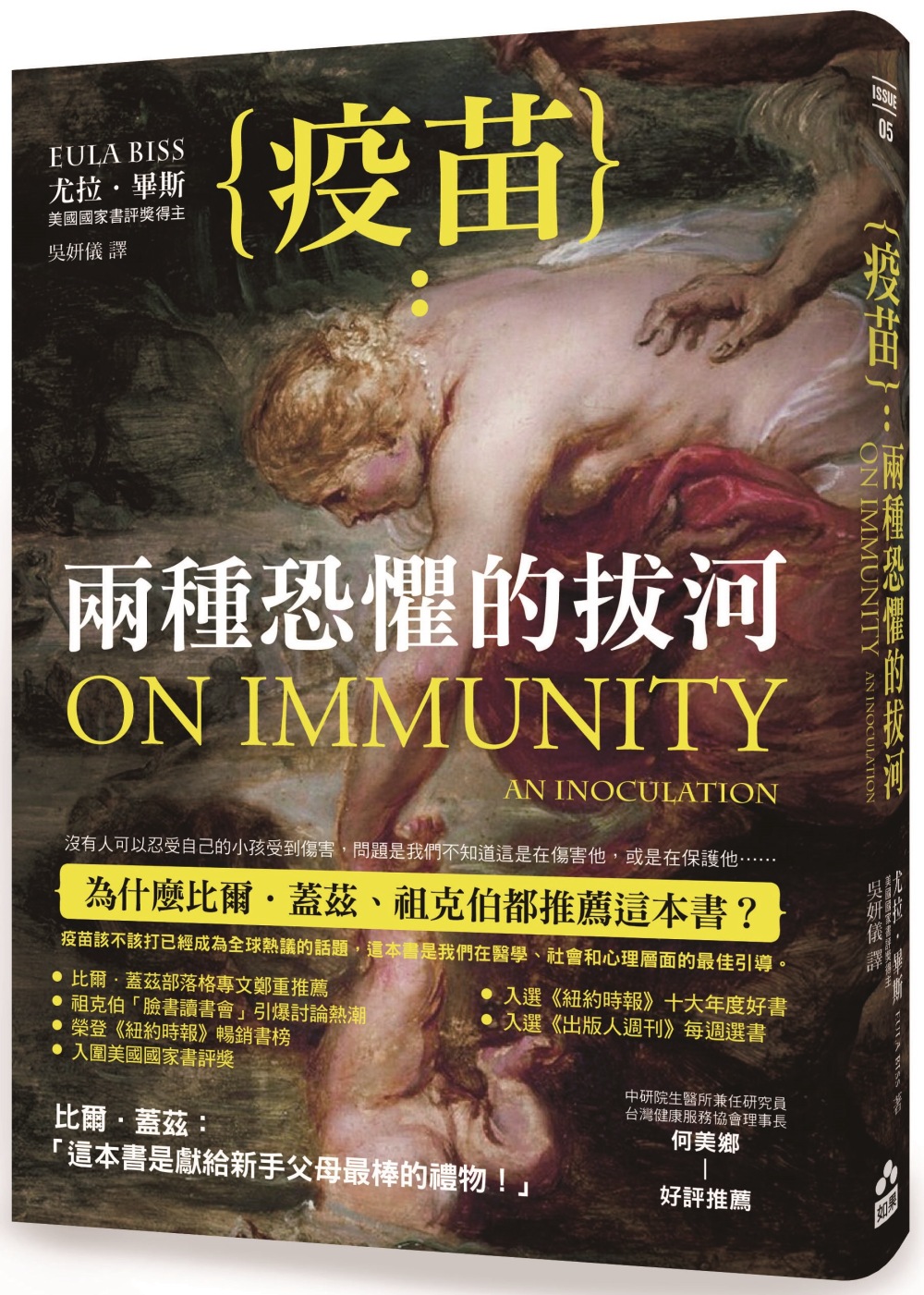 疫苗:兩種恐懼的拔河
疫苗:兩種恐懼的拔河 產業自律性管制
產業自律性管制 品格與品德
品格與品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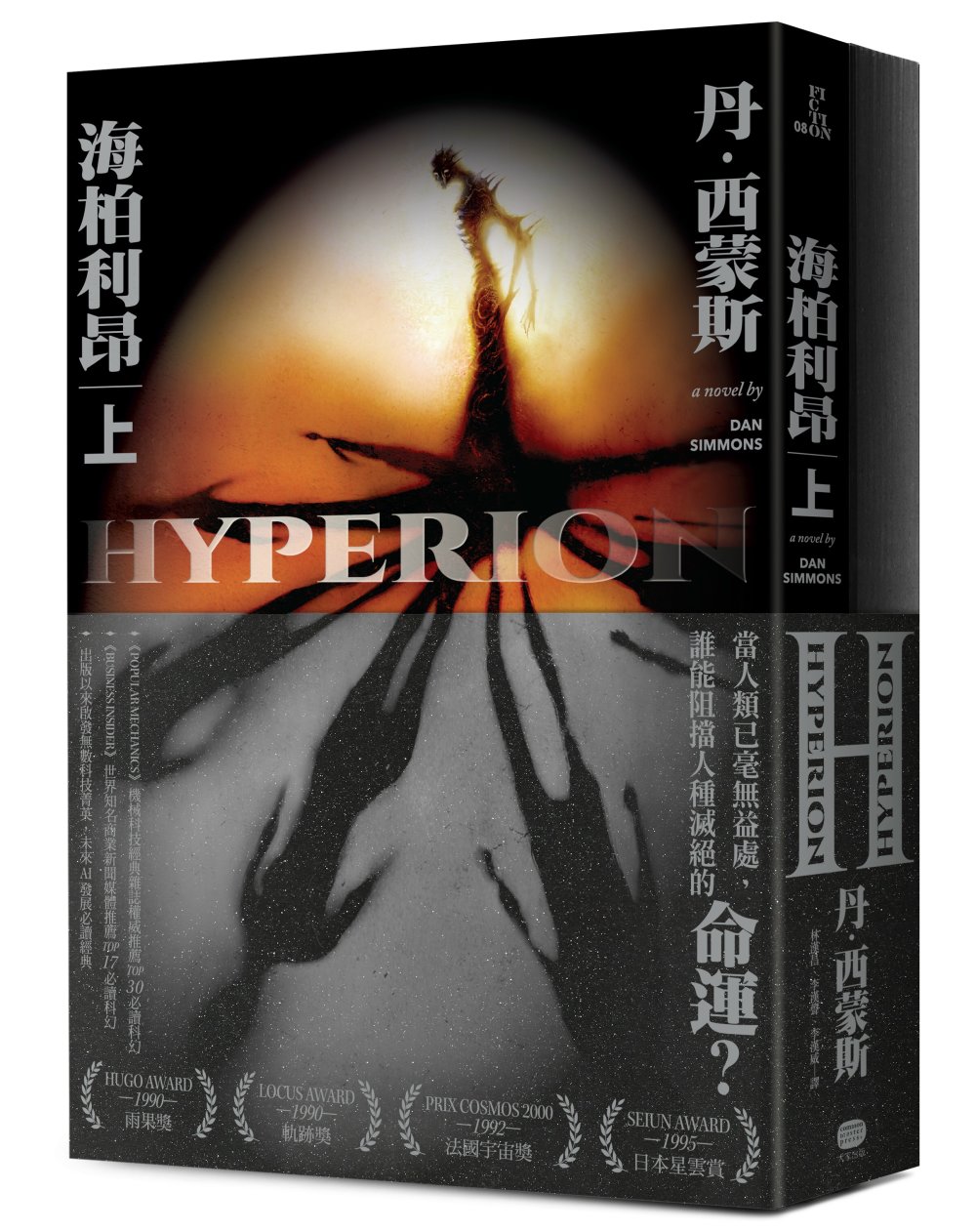 海柏利昂1(套書不分售)
海柏利昂1(套書不分售)